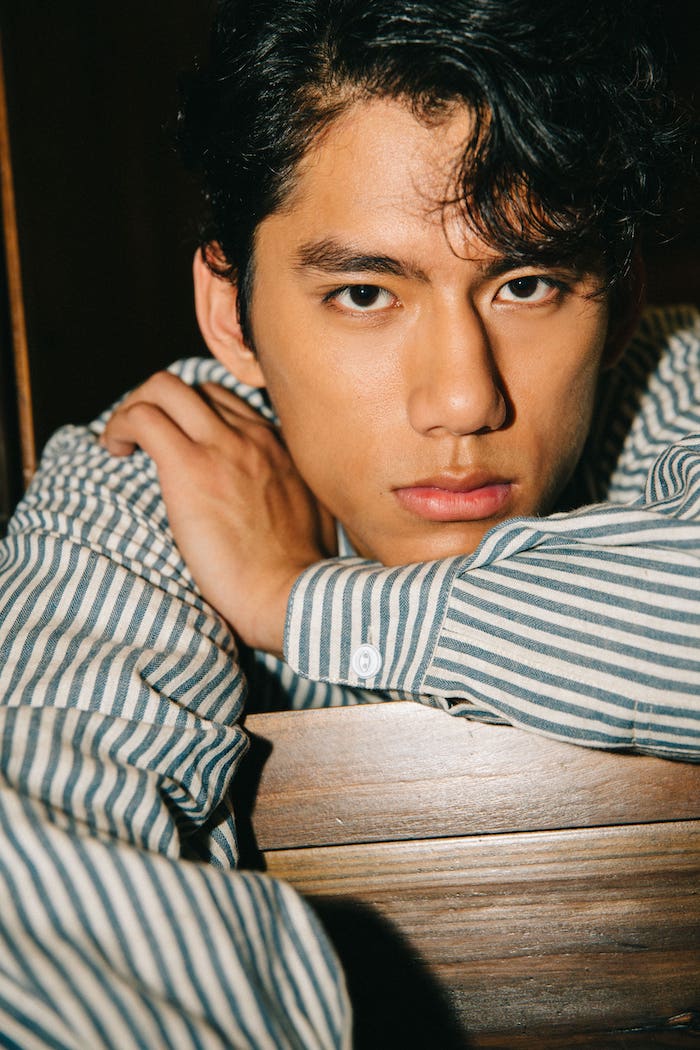游安順 ╳ 朱軒洋 ╳ 李英銓——做戲精也做自己,最佳男配角的提味學|2020 台北電影獎
13、21、52,三組年齡數字,既代表三位演員各自的階段風貌,也大致劃出去年度台灣電影在故事題材及人物族群上的廣度。入行 35 年的游安順在《第一鮪》的大浪上持續瞄準表演的精準度;朱軒洋在《下半場》以爆裂青春尋找對決之外、輸贏之外的可能;李英銓則懷疑,自己其實根本沒在演?戲裡的男孩阿全,更像他置換家庭背景後的小分身。

BIOS monthly 專訪三位入圍 2020 台北電影獎最佳男配角的演員,對表演的認識會因年齡、心境有所不同,但透過表演能得到的生命歷練擴充,於他們而言從未減少。
演員是狙擊手,享受切換的快感——游安順
從國劇練武青年,到各種戲劇片型通吃的小生,「戲精」已是游安順的第二個名字,亦是各大影劇獎項的入圍常客,去年以《野雀之詩》角逐台北電影獎同一獎項,今年繼續以《第一鮪》叩關,而甫播畢的電視劇《做工的人》,他又以「昌哥」交出令人驚艷的憨厚喜感。
眾人讚嘆他一身爐火純青的演技,他只說:「當你對角色有感動,你就知道怎麼詮釋並成為他。」

《第一鮪》全片在船上拍攝,上工前須從小琉球搭風帆至外海,再登上主景那艘遠洋漁船,每天那段時速五公里的接駁航程,沿途景色所觸發的體會,是他接拍本片最超值的收穫;片中與他有重要對手戲的印尼演員吉曼(Nue Najman Ade Putra),早先已在《做工的人》共事過,彼此增添一份熟悉和關心,也化作對戲時的助益。
回想 1985 年《童年往事》那個替侯孝賢發出年少聲音的「孝炎」、楊德昌《恐怖份子》裡不良份子的倨傲態度,電影定格住游安順的青春歲月,又一路目送他走入民視與大愛台的父親角色裡。35 年來,游安順的演員道路有迭有起,終至如今的游刃有餘,信手拈來,戲來就演。
不過,「把戲演好」僅完成演員工作的一半,日前因眼部急症登上新聞版面,他自責粗心卻也感觸良多:「演員一定要把身體照顧好,因為你沒有資格生病,一不小心就影響到製作單位。」
資深戲精的懇切忠告——戲裡是演員,戲外同樣不能鬆懈。

Q、準備一個角色時,會在何時何地讀劇本?讀本時有什麼習慣?
順:我自己的習慣是回家後,晚上睡前看仔細一點,看完不會一下就睡著,滿腦子都在想劇情、角色個性,再閉上眼睛安靜地做一些設定,那時候心才能靜下來,想著想著也許就睡著了,也許在夢裡還可以跟角色相見,他會提醒我應該做什麼事。這樣比較能沉澱吸收、跳脫自己進入角色。
Q、演員的修養大致可分為讀書、看電影看劇、觀察人類和自己,平時較常做的是?
順:剛開始接觸電影是拍侯導的片,20 歲之前的我每天泡電影院,一天可以看四、五部,那個時期看非常多電影;我也喜歡觀察一般路人——他在想什麼、為什麼會在這裡、等下要去哪——做個簡單的判斷,看看跟接到的角色有沒有雷同處;以前單身能享受孤獨時,很喜歡旅行、坐火車到處找朋友,那時陳懷恩(攝影師)介紹我買 FM2,拍了很多自以為的作品,以前非常文青,現在沒有拍了,人生目標不太一樣,反而是記錄小孩比較多。
Q、配角必須是稱職的綠葉,如何算得上稱職?常言「每座表演獎項只有一半屬於自己,另一半屬於你的對手演員。」本次入圍作品《第一鮪》中,哪場對手戲演起來最感張力?
順:以廚師的概念來說,配角除了陪襯功能,很重要是可以提味,不要搶過主角的戲,但可以跟主角產生共鳴,讓彼此更立體。
《第一鮪》我演輪機長,工作是維修船上所有機具,像軍中的輔導長,會看到每個船員的心理狀態,他精修精密工具,所以對人的觀察也很清楚,當印尼漁工受到些微霸凌、心理受挫、思念家鄉的女兒,又隻身處在危險的環境,我的角色有觀察到這點,所以試著去安慰他,讓他能跟大家相處,可是語言不通,只能講晶晶體英文,我自己講得有點靦腆,看劇本時也很擔心,但導演說這只是一種溝通方式,我就懂了,於是我更放鬆把所有英文字彙擠出來,我跟對手演員用肢體語言、表情、眼神來連結,反而是最直接的方式。
Q、演完一個角色,總會帶走些東西,也放下或留下些東西,是否有過這樣的經驗?
順:演完了就是斷捨離,其它的評價留給觀眾。當一個藝人、演員,最好是演完一個角色,觀眾有所省思、觀念有被影響,如果能做到這樣也算功德圓滿,只要有片刻的感動,留住一點點餘溫,是挺好的。
自己被角色影響的例子很多,要講拍大愛台戲劇的經驗,剛開始演病人比較多,好像把未來可能發生的狀況先走過一遍,心中都有種感慨──如果人到這一步會變成怎麼樣?之後我開始演師兄,要去幫助別人、為社會付出,戲劇好妙,給我各種機會扮演,又讓我學習成長。20 年前開始拍大愛,他們曾經對我過去的人生灰暗期不太認同,後來慢慢改觀,讓我重新站起來,所以我一輩子感恩,那是我安全的舞台跟港口,也讓我心境改變很多。

Q、近年你的產量不僅大而且還零失誤,今年除了北影,年初的金穗獎甚至有四部入圍,是如何達到演戲如呼吸般的境界?
順:我接到角色會畫個九宮格,用人格特質、生活習慣、心理狀態把每格填滿,這些不一定會在劇本裡呈現,但我會做個歸類,有些東西可能一直存在角色心裡,這樣就容易把個性的分析帶入表演,就算是拍短片,花的時間不多,但還是要有自己的見解跟輸入,把自己當成黏土。
前陣子曾經同時拍《做工的人》、《鏡子森林》和大愛戲劇,我會切換頻道切得很快,一天跑三組,戰鬥力越強時準確度也不小心越高,就像狙擊手,再不開槍就打不到了,所以瞄準速度越快,進入角色也很迅速容易,我是很喜歡忙碌緊急的狀態,神經都是繃緊的,會變得非常專注,這種切換是演員的快感,也是來自舞台劇經驗的間接助力。
一切的中間值在哪裡?——朱軒洋
以《下半場》雙料入圍「最佳男配角獎」與「最佳新演員獎」的 21 歲朱軒洋,銀幕形象頗有邪氣壞少架勢,他卻自稱是個傲嬌宅,需要多點時間適應環境和人際關係,於是演戲恰好成為一種心理寄託,「我今年開始想改進,如果把個性極端化,可能會忘掉很多事、一直活在自己的角落,現在想出去多摸點東西。」
這也是他沒專攻表演,反而讀服裝設計的原因,還被愛好園藝的爸爸間接影響,在學校選修了花藝課,「就像演戲一樣,我也可以把心情寄託在植物上;老師說每天重複做一件事,比如用同一支筆、喝同一種飲料,養成習慣就會培養出魅力。」不久前才入手一台八○名機「YAMAHA追風135」的他,認真想拓寬自己的疆域、打開門迎向世界。
《下半場》帶他認識事物的多元性,殺青不久的新作《天橋上的魔術師》則教他理解鏡頭和影像語言;是每演一個角色就成長一些?或是因為長大了一點才接到更成熟的角色?他發現演員與角色之間,就是這樣相互影響著,也在這樣的互相裡,成為更完全的自己。
朱軒洋,一個正督促自我向外伸展的男子。訪談結束前,他叮囑我們在文中幫他徵求學生作品演出機會,「我很想演學生獨立製作啊,但都沒有人來找!」是動是靜,熱鬧或寡言的角色都好,盼有緣劇組盡速與經紀公司聯繫。

Q、準備一部電影時,會在何時何地讀劇本?讀本時有什麼習慣?
軒:在家裡自己讀,我讀得很慢,看文字會想像畫面,想要透徹一點,太深入進去會變得沒那麼客觀,我就會去問朋友、家人,想知道更多人的想法,但有時候找不到答案。最近看到二元論,講靈魂的需求和肉體的需求,演戲時會不太知道怎麼達到中庸,做事也是,最近在思考這件事。
Q、配角必須是稱職的綠葉,如何算得上稱職?本次入圍作品《下半場》中,哪場對手戲演起來最感張力?
軒:用食物比喻:第一個想到的是珍珠奶茶,如果很厲害的奶茶,珍珠卻是硬的,整個就很扣分;就算已經是品質很好的牛肉,加上海鹽也會更和諧。就是「團隊」的邏輯吧,打籃球也是,光是自己很強沒用,要有好的隊友。
《下半場》最有張力是在醫院樓梯間打架那場,演戲有時候很高興,有時候很難過,但那天是難過得很快樂,任何情緒到達一個點之後成為水平線、休息安靜的感覺我很喜歡,對手少勳(男主角范少勳)很棒,導演也有種魅力,有時演員不知道自己要幹嘛,導演會給我們安心感,但又保持距離,讓你有適度的壓力把事情做好,我很喜歡跟阿吉(張榮吉)導演的相處模式。
Q、少數新人如你的幾位同門師兄是一出道就演主角,而你在首部作品《有五個姊姊的我就註定要單身了啊!》是從小角色演起,這是好的磨練嗎?有哪些幫助?
軒:是好事,因為我是比較急躁的人,需要緩下來,配角可以學很多前輩做事的態度,不用一開始就承受那麼大的壓力。
每個人都想當主角啊,但我覺得沒有永遠的主角,所以精神跟態度非常重要,只要態度對了就沒問題,而且當配角有很多戲演。
Q、連續演出《下半場》和《極限17:扣殺》兩部運動類作品,「姜桐豪」和「季志航」的人設也有點類似,都是自視較高、目標導向,你怎麼理解這樣的人格特質?
軒:他們兩個很像,只是季志航看起來比較像壞人,姜桐豪比較像好人,但本質是一樣的,都是為自己爭取而已,根本沒有錯啊,每個人都要顧自己吧?
自私是這兩個角色的樣子,也是我的一部份,必須把被討厭的樣子給大家看。季志航是裝腔作勢的人,他其實很膽小;姜桐豪比較無私,但沒有把關係處理好,可是本來就很難處理,總是不小心就變成壞人。

Q、演員往往是劇組裡最需要勇氣和安全感的人,誰給過你對於表演的信心?或你如何找到自信?
軒:我覺得無形之中大家都在幫你,你以為是自己努力,但其實是身邊的人,除了導演,像燈光、美術、後製、配樂、經紀人等等,只是演員當下不會發現到。
這也不算演戲吧?——李英銓
李英銓今年 13 歲,參演《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是他小五升小六暑假的事,徵選上角色時他打了退堂鼓,多虧老師和媽媽鼓勵,最終收獲難得的拍片體驗,還將金馬獎、北影獎兩個男配角提名雙收入袋。
劇組依據他的特質和經歷打造「阿全」一角,包括喜歡拍照、親近自然,以及先天色弱,他清晰地解釋這種狀態如何顯現於行為:「比如在牆壁上要找出有保護色的動物,一般人會看牠跟牆壁的顏色差異,但我找的是形狀,我的角度會跟大家有點差別。」
阿全是貫穿全劇的重要角色,圍繞在大人的悲劇之間,卻懷抱孵出一顆蛋的純真期待。對戲的阿嬤呂雪鳳、阿公張曉雄、媽媽李夢都已在舞台上千錘百鍊,第一次演戲的李英銓坐落其中,以自己的清澈天然,舒緩眾人崩解的局勢。
這位沉穩的小少年原以為去年電影宣傳期後,就會與電影完全切開,回到單純的學生身份,因此得知再度入圍北影獎的當下,第一個反應是「還有喔?」高興的那種,誰叫電影魅力無法擋呢,聽他說「如果導演找我去演路人,我絕對會去!」便知道了。
Q、片中你擔任旁白,演出時有沒有不太理解的內容,或是記得最深的一句話?
銓:錄旁白之前先讀過稿子,把一些文字改成我平常會用的詞,再去錄音,我會錄很多次,也會看很多次,也跟導演和副導討論台詞,印象最深的一句是「人生如果沒有了記憶,那這一生到底還算不算?」我那時也想了一下,我覺得還是算,因為我還是活過了。
Q、你的角色「阿全」對許多物件和生物很感興趣,比如火雞蛋、蝌蚪、玩具、阿公的相機,你自己也對這些東西好奇嗎?
銓:片中有兩台相機,數位那台是我自己的,底片是導演的,我只用過數位,以前滿喜歡拍照,但現在生活只有家裡跟學校,就沒拍了;我在戲裡有超級多玩具,有大概一半是佈置主景時我從家裡帶過去的,擺好後劇組再準備一些,把櫃子放得滿滿的,我都會拿來看看玩玩。
我以前讀的國小在山裡面,自然生態很豐富,一到五年級看過很多次蝌蚪變青蛙的過程,所以對蝌蚪的好奇心並沒有非常強,可是火雞蛋就是新鮮的東西,所以非常好奇,後來才知道我剛開始在玩的那顆蛋是孵不出來的。

Q、片中哪場對手戲讓你最有印象?
銓:有一場我跟阿公但被刪掉的戲,阿公的設定是會亂丟東西,我要負責去找,但要找得很自然;還有帶著阿公出去但看到火雞哥,我就趕快跑去追他要那顆蛋,結果阿公就走失了;還有一場戲在吃飯,劇組在地上倒水,我撿東西時要大叫「阿公尿尿」。這些演了很多次所以印象很深刻。
Q、初次演戲覺得好玩嗎?是怎樣的經驗?
銓:跟一群完全陌生的人相處在一起,慢慢去摸索、熟悉運作的過程和裡面的每個人,像導演就會去追求他想要的完美。
我理解的演員,是把別人的想法、寫出來的劇本去實際化,其實我也不算演戲,就是把自己平常的反應套在上面,因為我們沒有劇本,都是導演跟我們說等下會發生什麼事。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的感覺是,原來整部戲長這樣!片中家人都有自己的祕密,但是不敢講出來,我發現原來各種模式的家庭都是有的;每個演員都有讓人覺得厲害的地方,像阿公他真的可以把阿茲海默症演得很逼真,雪鳳阿嬤在市場爆氣,也讓人感覺她真的在生氣。
開拍前有一段跟其他演員相處、變得比較像家人的時間,假日時,在主景附近或是導演工作室煮一頓飯一起吃,吃了滿多次的,也都有攝影機在旁邊拍我們互動,所以就習慣攝影機是一個物品。最有趣的是開拍之後,一間小小的房子,我們六十幾個人,超過一半擠在裡面,夏天很熱,冷氣會影響收音就關掉,大家都這樣為了一部電影。


採訪當天,現場多路人馬熙熙攘攘,在緊密安排的時程中,游安順、朱軒洋、李英銓在兩層樓間上上下下卻氣定神閒。鏡頭來了就拍,需要等待就耐心佇足;中青少三人同框,雖是競爭對手,竟別有一番溫馨和諧感受。


2020 台北電影獎
日期|2020.07.11 (Sat.) 19:00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