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他媽的千憂解寫他媽的詩──專訪陳黎
2011 年 11 月 14 日。陳黎清楚記得這一天,「第六屆太平洋詩歌節」結束次日,所有痛苦從這裡開始。那天右手、右背突然劇痛,匆匆趕去醫院,醫生說他是筋膜炎,一般來說按時吃藥復健就會康復。但沒有。後來他轉去大醫院,醫生開給他類固醇藥,炎症才得以消退,然而其他病痛卻命運般降臨:腕隧道症候群、骨刺、左膝拉傷⋯⋯那時他連滑鼠都按不下去,更別說寫字,最慘的日子裡胸口痛到無法開車,不能睡覺,被迫吃安眠藥,半夜會突然哀鳴,從肉身痛進靈魂,不到半年從神經科轉去身心科,2012 年 3 月開始服用千憂解。如此病痛折磨了他一年多。
陳黎說他曾經是想死的。
.jpg)
.jpg)
死結
採訪前我翻出 9 年前的國中國文課本,翰林版,〈聲音鐘〉。課本裡作者簡介喚他是文學的夢幻騎士——騎士現身,沒有盔甲,沒有馬。反而穿的是格子襯衫、卡其褲,披一件皮外套,踏著涼鞋而來。陳黎頭髮比課本裡的作者照白,他今年就要 70,一下子〈聲音鐘〉已經是 35 年前的作品。
35 年,幾近是他的半生。
時鐘,日曆,月曆。這些美妙的叫賣聲,活潑、快樂地在每日生活的舞台裡翻滾跳躍。他們像陽光、綠野、花一樣,是這有活力的城市,有活力的人間,不可或缺的色彩。
我喜歡聽那些像鐘一般準確出現的小販的叫賣聲。
被〈聲音鐘〉拉拔大的我們這一輩,或多或少記得課本裡還有小汽車與錄音機,有「嬌滴滴」的註釋要背,以及最好吃的美心冰淇淋蛋糕。可在被時間乾燥過的課文外,陳黎繼續活,有段時間,他恨起了聲音鐘。
12 年前詩集《妖/冶》出版,前言回憶 2012 年最慘的那幾天裡,附近國中七點半準時響起〈念故鄉〉的旋律、妻子準備好早餐端著上樓的腳步聲,他都恨,他好恨,因為他知道自己又得起床與妻子對坐,吃飯,除了抱怨病痛,什麼都做不了。
「你說我像不像一個囚犯又要吃藥?」那時一天動輒十幾顆,幾個月下來看診逾兩百次,連健保局都來電關切。他頻繁掛在嘴邊的是:度日如年、痛不欲生。痛到最底部,他對自己絕望:「我那個時候感覺到的,就是一種受困。好像我真的走不出來了。」

2012 年底,陳黎受邀代表台灣參加英國舉行的奧林匹克詩歌節,早答應對方、機票也買好了,卻為大病所犧牲:「那時候痛到連花蓮火車站都沒辦法去,怎麼可能到倫敦?」
很難想像這是陳黎。曾經搭高鐵從南到北趕演講、評審,一年下來活動百場起跳,策劃太平洋詩歌節近 20 個年頭的陳黎。
他自嘲,不需去倫敦,病情已經夠「奧林匹克」了。「你有沒有看過那五環?就像連環結一樣,彼此交纏。手痛,痛到無法自己綁護膝,無法綁護膝,所以也不能下樓出去,只能每天在樓上床鋪上,很無聊嘛,也沒辦法轉移注意力,一直痛一直痛⋯⋯」
「你就變成一個死結。」
.png)
另一個結是藥。2012 年 3 月,他開車時胸絞痛,得靠安眠藥才能入睡。有次妻子在他劇痛所發出的慘叫中驚醒,天未亮就開著車,載他到大醫院掛號。
醫生開給他七顆千憂解,一禮拜的量,馴養痛覺。起初他不願吃,害怕被後半生被藥奴役,害怕吃藥就是向生命屈服。但能怎麼辦呢?痛到臨頭,尊嚴最沒用。他打給幾個作家朋友,諮詢過精神科從醫的王浩威、鯨向海,是他們相勸,他才終於吞下第一顆。
「那哪是千憂解?根本是千憂結。」
又一次他打給鯨向海:「怎麼會這樣?我吃了沒什麼感覺,還更焦慮。」鯨向海再勸他繼續吃,如果還痛,那就照醫生說的,每天藥量增添到兩顆。期間他便秘、尿道變窄、頭暈⋯⋯副作用來得比療效更快,藥的詛咒總是先於祝福。
一串串死結,最後是在吃一陣子的西藥、以及中醫看診間,才徐徐解開。「醫生幫我針灸完,他就說,『你等下把護膝拿掉,我保證你上下樓梯不痛』——我想說怎麼可能?」
制約的自由
沒想到還真的可能。
中醫治療下,他終於可以踏出床、踏出家門、踏出花蓮,心神也澄澈起來。病暫且是停了,他把這段從苦病到康復的文字產出,集結成詩集《妖/冶》——所謂妖,那當然是病妖。
書裡有 219 首「再生詩」:他圈出過往詩集既有的文字,以這些文字重組成新的詩作。鯨向海在序裡說他「奮力用詩救贖自己」,但救贖的基底,是一層苦勞與無力感。
之所以選擇圈字作詩,不是以形式為由貪方便,而是患上腕隧道症候群,手動不了,「那時候真的很困頓啊,沒辦法寫,會痛,只能夠用左手圈字,圈好字,叫我太太幫我打。她有時候會誤打、誤讀,我也不管,就當作是她幫助我書寫、或上天幫助我書寫的一些印記。」
圈出一個字的範圍,已是他最大的領域展開。
陳黎的詩以形式多變著稱,最為人流傳的〈戰爭交響曲〉透過「兵」「乒」「乓」「丘」的字符轉換嘲諷戰爭,〈一首因愛睏在輸入時按錯鍵的情詩〉純愛裡雙關了心照不宣的情色。一路上,他大膽地挑戰既有的詩歌形式,但以前大膽是因為好戰,如今大膽是不得已,是因為病。
「當然有一個部分,也是因為身心狀態的轉換,激發以前沒有的那個東西——的確是有一種激情在那裡。」激情,來自另一位作家好友莊裕安的諫言:把《馬太受難曲》的「受難」(passion)化為「激情/熱情」(passion),用殘骸開出紅花。「你被病所束縛,所以有那個苦難/激情想要透過書寫去克服某些東西,讓某些東西可以度過。」
也包括死亡。
「命都快沒有了,我還怕違反什麼風俗善良嗎?面對死亡,面對某種斷絕,你思考的方式會變,會對某些事情無所謂,你會有不一樣的勇敢跟大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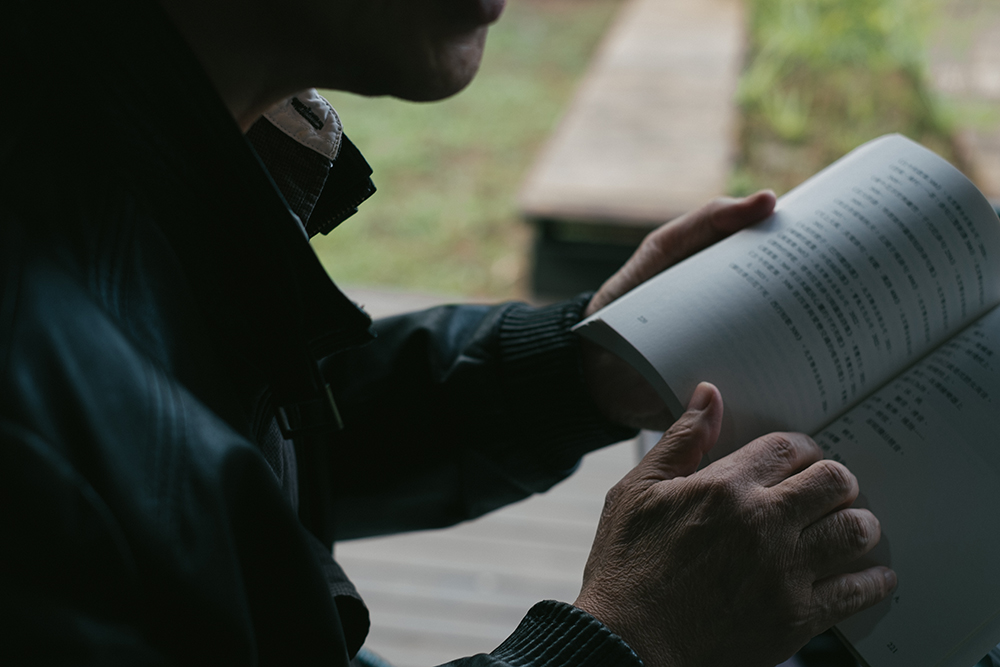
疾病迫使陳黎意識到肉身,自己真正被肉身所禁錮,「活著是一種制約,但有時候是越制約越自由。」這點也適用在創作:「我們常常會覺得說,古詩、五言絕句,被格律所限制——可是當我開始創作,我才知道說,格律其實不是限制,格律是想像的跳板。因為它限制住你,當你選的字很有限很有限,那你只好用那些平常不會寫的字。」
他指著菜單:「如果要你從上面選字,寫一首情詩,你會怎麼選?這裡面甚至沒有一個『愛』字,你只能用 cheese cake 代替。」
「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可是如果地上只有屌跟屄合乎格律,你要不要寫?」
生命的懸崖,他重新鳥瞰一生的創作,「別人看我的詩,好像很大膽,但其實每一首詩,都是有格律的,都是節制。」去年剛出版的第 15 本詩集《淡藍色一百擊》裡,〈金閣寺〉也主動戴上腳鐐跳舞:
.png)
這首詩要拆去「金」字旁,才能讀出原意。曾被束縛住的,紛紛踮起了腳尖:「你看我們,現在就像詩裡寫的『良朋同坐』,今天你們專門來看我,我覺得非常好,可是半年前我的學生來看我,我從頭到尾都在緊張,一直拉肚子。就是焦慮啊,身心症啊⋯⋯」
他說,「如果再早個半年,我是不可能答應你們採訪的。」

不痛了
2013 年出版第 13 本詩集《朝/聖》,書名也明喻了他信徒一樣的苟活,尋醫如求神,看病像問卦,治療後,不敢說從此歌舞昇平,但至少,不痛了。
不痛了。他不會說那是奇蹟,但確實幸運,幸運讓他害怕,怕萬一,怕幸運不夠了怎麼辦?從《朝/聖》拿下台灣文學金典獎開始,劫難後的 9 年裡,陳黎與妻子張芬齡又先後合譯了 20 幾本詩集,包括普拉絲、瓦烈赫、聶魯達、辛波絲卡、松尾芭蕉⋯⋯而他與他的作品又一次出了花蓮,巡過美國、希臘、新加坡、法國、義大利、韓國⋯⋯,太平洋詩歌節也順利辦下去。
「我好像又活蹦亂跳了。」直到 2022 年 10 月底,太平洋詩歌節前半個月,陳黎染上了俗名「皮蛇」的帶狀皰疹。
醫療網站對皮蛇的描述大抵相同:不致命,但高機率使人痛苦不堪。
陳黎指著自己的左臉、左眼,「以前筋膜炎、骨刺痛的話,就是痛痛痛痛痛;可是這一次得皮蛇,是隱形的、軟的痛。更深了。」一開始感覺眼周在滴水,接著慢慢凝固,變成眼罩,「最後嚴重了,像是戴了一個面具、很硬很硬的面具,在臉上。」
醫生暗示他三叉神經恐怕遭到威脅。有次讀台大醫學系的學生回來找他:「老師你要有心理準備,這可能是你要終生與他共存的,以十年、二十年為計的抗戰。」
十年以後、二十年以後。他不敢想像那時的自己是什麼樣子。

對痛苦的恐懼,比痛苦更像痛苦。巨大的焦躁讓他不得不吃藥。先是「黃金之藥」利瑞卡無效,反而眼皮持續鬆垂,身心科醫師改開了抗憂鬱、焦慮的萬憂停、安邦,一次次換藥的過程,卻讓面具箝得更兇。後來才下定決心吃回千憂解。吃藥的日子,他形容是地獄的再訪:
我曾對醫師說今年上半年服「萬憂停」等抗憂鬱、焦慮藥過程,於我彷彿是下地獄,把我修理得不得不(不)甘心接受「肉體」之疼痛、不適,以保住我的「心」、我的小命。
去年,不知道是不是藥效終於起作用,皮蛇慢慢溜走,結痂,留下黑色素沉澱。如果不說,旁人不會看出那是他與皮蛇纏鬥的戰疤。

「不過現在比較好了啦。你看我現在沒瞎,視力也還好,看起來好好的。」縱然沒照到的地方,暗翳仍舊:「⋯⋯但我剛開車來,還是覺得,應該要點個眼藥水再出門。」
陳黎說他曾經是想死的。
現在他會說,是不想活了。
沒什麼意思嘛
「出書其實是哪時候都能出啦,只是這次,好不容易撿回一條命。」原來《淡藍色一百擊》也是戰疤。
「我也九年沒出詩集了,有些讀者覺得我的一些詩太前衛,或遊戲性太強,但我覺得我每一首詩都是嚴肅的。這次寫了十多首『病中作』,比較悲苦,多少會平衡那些讀者對我詩作的印象吧,不覺得它們全都吊兒郎當。」
或許可以老套地說「文窮而後工」。苦難裡,他仍把詩寫得幽默。陳黎在訊息裡說他身上永遠住著一個頑童,七十二變的孫悟空,「只要這個頑童、這個赤子之心不死,我的生命就在,我的詩歌就頑強地活著,變化著⋯⋯」
可是,孫悟空再蓋世,也曾被佛祖壓在五指山下。「我的個性比較自我、好動、靜不下來,常常被人說是無法無天——當然年輕的時候比較可以為所欲為,可是老了,病了,它會暫時剝奪自由,我就不習慣了。我發現人真的不能去跟天怎麼樣,哪有無法無天這種事?」
「我那時候對存活是不抱希望,就覺得,活著沒什麼意思嘛。回頭看以前寫的某些詩,我會覺得是很大的諷刺。」他翻書,指著這些詩:
我的父母親,今年加起來一百八十歲
雙親如雙星,高照浮世上的我,讓過了花甲
之年的我這個花蓮路人甲想變老、稱老,都
變得有一點難⋯⋯——〈七星譚〉
「當時我還可以自我調侃,我只是花蓮路人甲,怎麼是花甲?花甲這兩個字怎麼可以用在我身上?」看他前幾年在〈我們在島嶼朗讀〉的拍攝,頭髮烏黑,不像領過敬老卡。「本來六十歲我都嫌自己老,但生病讓我一夕之間老了二十,現在身體狀況都像八九十了,這樣一種衰老一種無力,讓我很痛恨這些詩。」

曾經詩裡形容父母像牆,為人們遮擋死亡的車頭燈,但,「過去一年我一直強烈地預感,我會比我的父母早死,看到先前這些詩,我覺得非常難過。」
他沒想過,自己會被自己的純真、被自己擁護了一生的美學懲罰。
補紀念紅寶石婚的〈星宿海〉與〈雲夢大澤〉於他,都是太童話式的書寫。對痛苦裡的人來說,童真是種薄倖:「用一個超現實或夢幻的手法,來寫說我老了、我死了之後,跟我妻子的一些情況。用童話來淡化死亡的恐怖。問題是,現在看,寫得太美了吧?太浪漫了吧?滿搞笑的。」
他自嘲是妻寶,不能沒有妻子打理、照料,這也令他羞愧。十年前病痛時,出版社詢問他們願不願意翻譯普拉絲的詩集,「自白派的普拉絲,她的詩痛苦的密度很高,翻起來非常辛苦——我太太居然答應了,她其實是不太想做事情的人,卻願意翻她的詩⋯⋯」因為相較照顧他,譯詩是妻子一天裡少數能喘口氣的時間了。
我的妻,吾妻,是一座
港:梧棲港,收容漂流、浪蕩的
我這條木舟,讓
吾終生
棲身其中——〈我的妻〉
他說這詩似乎肉麻,「但肉麻是因為你根本沒辦法選擇,你情何以堪?她這樣子累。當然我還是用吾妻/梧棲這種機智幽默去騰出一些詩的美學距離——但如果可以,誰要寫那種悲慘的詩啊?」
去年七月寫〈大招〉,以《楚辭・大招》裡的「魂魄歸來!」貫串全詩,「大學聯招資格摘要——/靈魂學組:領有重憂鬱、重焦慮機車,或恐慌與腸躁/聯結車駕照者等;」把痛苦當成學分來修,他不再迴避,「這簡直是在自虐,把自己的疼痛分組,還得替自己的困頓招生,招生嘛,招新的生命力。」
同時期〈與蛇共舞——並反歌一首〉與皮蛇直球對決。騎士卸下鎧甲,裡面那麼多傷:
每一日我都有想殺死你的願望
也都有想死的願望
從風到風景
〈與蛇共舞——並反歌一首〉師法日本《萬葉集》中的「反歌」形式,在前面的長詩接續另一首短詩,作為對原本內容的簡述或挑釁,戲謔的重新戲謔。而這首反歌恰恰呼應了詩集名稱,《淡藍色一百擊》:
淡藍色一百擊:如何擊重成輕,以
一擊一擊漸淡漸輕藍色電波,擊打我
拷練我,成為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輕
「醫生說我是『努力在生病的人』我就說,對呀,我真的滿努力在生病。一擊一擊,讓深藍色變成可以承受的輕。我現在就是可以承受了,才敢面對你們。」他說,「其實醫生叫我不要去談這些東西、不要再想過去⋯⋯」但他畢竟是陳黎。
.jpg)
他形容過去自己是一人馬戲團,亂彈亂唱,自成一團,「可是現在是真的有殘缺啦。但是起碼我覺得還可以跟它共存。」詩集最末是一首延長音〈山水〉,他援引幾句:「而且你看我現在跟你們講話,還是嘮叨個不停嘛,殘響不絕,活生生在。」
活生生在——他閉眼,讓風流過。
下坡路上,涼風徐來
天藍,然而走在樹蔭裡
——竟有這等好事!——〈淡藍色一百擊〉・17
「你看,涼風徐來,哇噻,讚啊,但他媽你困頓困得要死的時候,你連風都沒有感覺的時候怎麼辦?」他又寫下〈如歌〉,彷彿是對晚年的一擊反歌,生活的重新生活。
黑夜變成白日
白日變成象牙白腳趾下如歌的行板
風變成有感覺的風景
詩人變成日常人——〈如歌〉
「我那時候就坐在星巴克窗外,看遠處的山,卻什麼感覺都沒有,我真的、真的很想要成為一個有感覺的人。」連感受風都嫌奢侈的生活,他也想知道自己為什麼活成這樣。「這首詩我寫完就哭了。」

「所以謝謝你,你們來讓我知道,我還是可以再走出去,明白『回到日常』原來不是太大的困難。雖然不像以前手腳靈活,可是起碼,不必讓自己浸在悲慘跟困頓裡頭——」他笑了:「雖然我還是覺得,我他媽的怎麼這麼衰。」
現在他每晚十點多就寢,隔天六七點醒來,盥洗,換好衣服,滑一下手機,出門去家門前 100 公尺的星巴克,點咖啡、用早餐,近午就在星巴克外的小廣場走走,往上看,風搖動葉子篩落陽光,「那就很像千萬隻樹葉的眼睛,在眨。就好像在召喚我說,『欸你趕快趕快啊,跟著我們把眼罩、面具甩掉』。」下午去茶舖坐坐,他迷上 70 元一杯的珍珠綠茶,晚上回家,處理新的翻譯工作,閒暇時就追追劇,最近不太需要去醫院了。
我問他還有在寫嗎?他說有。
曾經詩為他撿了一條命,剩下的日子,得繼續寫作來還。
.jpg)
.jpg)
《淡藍色一百擊》
作者|陳黎
出版|黑體文化
出版日期|2023.12
.jpg)

%E6%B7%A1%E8%97%8D%E8%89%B2%E4%B8%80%E7%99%BE%E6%93%8A%EF%BC%BF%E7%AB%8B%E9%AB%94%E6%9B%B8%E5%B0%81_300dpi.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