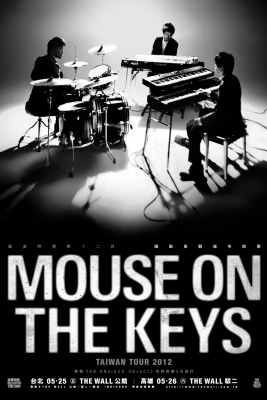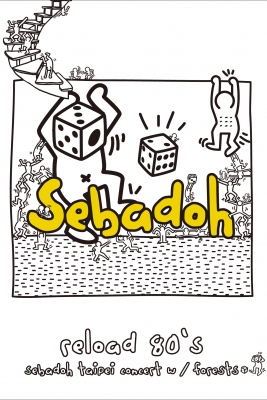【音樂餐桌|微醺】與世界正面下戰帖,我厭世我驕傲:新女子樂隊的即興之夜
繼電影與文學餐桌後,新生代女子樂隊的厭世力接棒上場!這次邀請到顯然樂隊主唱阿琺、老王樂隊大提琴手佳瑩與孔雀眼主唱令晴,三人一手啤酒三首 Jam(即興合奏),在酒精與音樂的微醺之中,大方說出厭世心裡話。
聽聽三位獨立樂團少女從青春期變形而來,各種尚未完熟的人格,在急於與世界碰撞的渴望,與現實和理想的落差之間,迸發出一條條伏流著的厭世少女心。
|
左起:孔雀眼主唱令晴、老王樂隊大提琴手佳瑩、活動主持人芷儀、顯然樂隊主唱阿琺 |
厭世是青春期的必破關卡?
回想起成長過程,高中時期的令晴賀爾蒙作祟,心緒特別浮躁:「我覺得青春期對自己的不滿意,是因為找尋自我價值和定位的過程,會覺得對自己有很多疑問。」因為對自我的不了解,產生對這個世界的格格不入,最後轉變成一種厭世的情緒。
從小出身音樂班的佳瑩,則視自己的專長為厭世發源地。每天放學就要馬上回家練琴,甚至在新崛江旁讀了三年國中卻從來沒去逛過新崛江:「我每天只要想到,天啊!我要練琴了,就會覺得好煩喔。而且當你看到其他同學都在進步時,明明做一樣的事,自己卻沒有什麼成長,就會開始覺得人生怎麼會長這樣?」她自嘲開竅得晚,到了大學才知道原來這樣的心情叫厭世。
很早就接觸到日本文學家太宰治的阿琺,有著比一般小孩更為敏感的神經:「我一直沒有很確定這個詞(厭世)確切的意思,好像在日本文學裡面厭世有一個傳統,例如太宰治。小時候看到厭世不能理解,當時的世界就是家庭、班級、學校、補習班,但我喜歡從家裡窗戶看著其他亮著的大樓,在晚上開始想:不知道其他小孩在幹嘛?」雖然當時讀不懂太宰治,卻擁有老靈魂的早熟:「這是用自己有限的經驗去揣摩和我們不一樣的時代背景」。
|
|
厭世的人,你們在厭什麼?
維基百科顯示,厭世(Misanthropy)這個詞起源從希臘文μῖσος(仇恨)與人類ἄνθρωπος(人),是一種對人類本性仇恨、不信任或不屑的感情。Google 搜尋厭世,第一個搜尋結果是「需要協助嗎?台灣: 1995 生命線協談專線」, 24 小時全年無休。那三位音樂人又是怎麼看待厭世標籤的呢?
阿琺首先開了第一槍:「有沒有人可以創造一個什麼後厭世?我很期待這個東西出現,因為厭世已經太常被談了,我一直在想像後厭世會是什麼樣貌,它是要去辯證什麼。」僅管顯然樂隊被貼上了厭世樂團的標籤,但阿琺並不認為自己的音樂是厭世的表現,「所有文化現象就是不斷在兩端之間擺盪,復古之後前衛,前衛完再復古。」
有感近來的憤青文化越來越流行,令晴回道:「大家保持獨立思考很重要,就是你憤什麼?社會對不起你什麼?還是我們可以從自身開始做起。」然而只有一點會讓現階段身心皆處 peace 的令晴抓狂:「我最憤的時候就是開車的時候!我有那個怒躁症,有些人看起來平常很溫和,但是他只要一開車或騎車,就會變得超憤的~我就是那種,有人超車的話我會在車上大罵三字經⋯⋯覺得你們需要被教育如何正確的使用交通號誌!」
|
|
「我看厭世是一種挫折。當你經歷到了(挫折)可能開始會逃避,或者是有苦難言,就像我們可能經歷到社會不公義、社會腐敗,或是自身經歷。」仍在大學生活中,佳瑩的厭世是一種成長過程:「因為經歷了,當你正面的面對它反而是一種成長,我覺得『哇我終於經歷到什麼叫厭世』,然後我正在面對它。」
和三人邊喝啤酒邊聊完厭世價值觀後,眾人也開始進入了一些微醺狀態。第一首 jam 就以「微醺與生活」為主題,由阿琺的吉他、令晴的貝斯與佳瑩的大提琴合奏,現場即興演出,將黃湯下肚後的生活心緒轉為樂曲呈現。
首次合作的三人 jam 完像喘了一口大氣,與沒合作過的對象即興合奏,即使在開場前彩排過 15 分鐘,仍像是裸考一樣充滿未知、刺激又無處可逃。阿琺笑說:「真的要練(彩排)可能也不會練出什麼來,表演的時候完全是兩回事,我沒有做過即興這種事,還滿好玩的。」令晴倒是頗有心得:「我覺得剛剛有一個 magic moment,一開始有點乾澀的感覺,後面就濕潤了起來。」佳瑩附和:「那個 feel 就來了!」希望時間可以再多一點。
|
|
和標準說再見,以音樂為名走在反抗之路
有次阿琺在拍謝少年的演出中,聽到主唱薑薑說,「在西方的搖滾樂是在反抗一些體制或是壓迫,但在台灣玩獨立樂團反而很像是在反抗我們自己。」這段話像一顆燈泡一樣在阿琺腦中亮了起來:「他講那句話就解答了我長久以來的疑惑,就是大家為什麼都好像搞得這麼文青,到底大家是要反抗什麼?反抗自己也是一種反抗。」在社會化、標準化的成長過程中,存在著許多對自己的質疑,其實是在反抗那個想要標準化的自己。「如果標準不存在了,我可能就會反抗我不知道要反抗什麼。」
而加入獨立樂團,就是佳瑩對過去日以繼夜練琴生活的一大反抗:打破過去持續的生活步調和習慣,去嘗試一個不一樣的新的東西,是她心中反抗的模樣。「像我覺得我自己加入獨立樂團就是一個超酷的打破,你可想像我原本練琴就是是 Do Re Mi Fa Sol 這樣,後來變成超嗨的登愣愣~~那種感覺就超酷的欸!」
|
|
令晴對反抗的詮釋,則類似蔡健雅唱的「進化成更好的人」,對她來說都是個過程:「不管你是用社會的角度去看,還是用自身,因為反抗代表你對現狀不滿意,那你想去改變現狀,就表示你正在一個進步的過程當中,所以我覺得反抗是讓社會跟自己都成為更好的過程。」也因此在音樂創作上,她追求推翻過去的東西,朝新的可能邁進。
在音樂的啟蒙上,阿琺和令晴都曾受到艾薇兒的影響,而龐克文化則是啟發了阿琺對音樂嶄新的認知:「對我來說就有點像突然進入到立體派,我可以看到速度與流動,發現音樂居然可以被拿來不是要演奏一段旋律,而只是為了發出極大的音量,這件事情我覺得很有趣。」
令晴則是早在高中時期就先接觸到了 psytrance 曲風,多次參加深山裡舉辦的 psy party:「我也覺得很離奇,那段時間真的很常去,每個禮拜都去一次,有一群朋友都會丟活動,然後一起開車上去,那時候玩團,其他人都是大學生,我是唯一的高中生,他們開啟了我的 psy 趴記錄。」雖然旁人都覺得這是一段黑歷史,但令晴卻說這是不可或缺的過程,「那段經歷改變我很多,才讓我現在開始做電子。」
|
|
時間來到第二場 jam,原先的微醺也在半小時後漸漸走到茫的狀態。令晴和阿琺坦言在演奏的時候腦海裡浮現的都是 psy 趴場景:「大家都慢動作的在跳舞的感覺。」「我也差不多是那樣,藍色的天空飄著彩色的獨角獸。」
佳瑩則專注在彈奏的節拍上:「我剛剛在想說天啊我是不是太快了,我變成在拉旋律,我以為是我拉低音然後⋯⋯」沈浸在 psytrance 迷幻中的阿琺和令晴異口同聲:「我們都沒有在想這些啊哈哈哈哈哈!」
教教我吧!音樂少女的創作習慣大公開
Q & A 時間,眾音樂少年少女們對三位創作的問題接踵而來。歌詞創作方面,最近正在籌備新歌的令晴習慣先寫曲再把詞放到 vocal line 裡面,有時候則是唱 vocal line 時就順著氣氛把詞寫出來:「像〈VIVIAN〉是一次寫完,然後〈鮮紅〉就是拿著一本本子擦擦寫寫,擦到本子都快破掉了還是沒有很滿意。我覺得我好像不適合坐下來寫歌詞,不適合用寫詩的方式,我好像比較適合練團的時候一邊唱,然後把詞寫出來,通常這樣子出來的詞會比較自然。」
和令晴相反,阿琺通常都是還沒有曲先寫詞:「所以這就會滿難的,vocal 旋律性的發展就要跟著這個詞,然後充分的表達出這個詞的聲韻、節奏感,因為語言是一種音樂,所以不同的語言在不同的音樂裡會有不一樣的化學反應。」
|
|
她們也不避諱地提到,寫歌遇到瓶頸時找 reference、多聽一些作品是很重要的。令晴在寫一首歌的時候可能同時會有五首歌的 reference:「比如說大鼓的音色,或是段落上我想不到要怎麼做的時候,我一定會去找參考的東西來聽。」阿琺也說:「我自己很常偷人家的東西,但你不會聽到一模一樣的旋律,你不要回去找碴!」比起腦袋空空狂抽菸,多聽多看多學,是更實際突破瓶頸的方法。
編制大提琴旋律時,佳瑩會先定位自己在段落中的角色:「有時候一個搖滾樂團的編制,大提琴加進去可能只是想要一個聲響效果,那我就會思考自己的音域該被聽到多少,旋律需要那麼多嗎?或者其實只要一個音也很好聽,我會往這個方向去想。」沒有靈感的時候就到外面走一走,吃吃點心寬慰自己。
|
|
活動漸入尾聲,現場加碼安可一首 jam,此時三人的默契就像這首歌的音域一樣,比前兩首更高也更廣,阿琺與令晴一低一高的聲線交錯,佳瑩拉奏大提琴的優雅沈穩,空氣像是一波波海浪拍來,映的現場波光粼粼,新的女子樂隊彷彿就此誕生。
厭世的定義似乎已不是厭棄了自我、背離了世界,從三位音樂少女的厭世經歷及音樂創作,我們看到的是如蛇換皮一般,脫掉自我層層框架與世俗束縛後,活得更有力氣。
|
|
|
|
|
|
【微醺良伴】禾餘麥酒
這次活動除了邀請女子樂隊三人共襄盛舉,現場也提供禾餘麥酒妝點晚夜的微醺,以下是三款啤酒口味的自我介紹。
白玉麥酒:以淺色大麥芽為基底,加入大量與光復原住民契作的本土台南白玉米,以及烘烤成焦糖色的台中選二號小麥。白玉麥酒帶有淡淡的奶油與爆米花香氣,以及帶有蜂蜜甜味的清爽酒精濃度與酒體,味道柔和卻不失層次,適合搭各式的菜餚,易搭餐卻又不搶戲。
硬紅春麥酒:硬紅春麥酒當然加入了滿來自台中大雅的台中選二號生小麥、禾餘自製發芽小麥以及烘烤小麥芽,帶給你滿的麥芽口感。開瓶後由冷泡酒花帶出的松針、西洋杉香氣,隨之而至的是烘烤麥芽帶出的焦糖、太妃糖香氣,最後以令人發麻苦韻作為結尾。
月光麥酒:在德國大麥芽的基底中,加入台中選二號小麥、越光米在台改良種(台南 16 號)與台灣本土橘子,充滿鮮明的丁香、香蕉與柑橘香氣,在些許蘇打餅乾風味的襯托下,果酸味與甜味皆顯豐富,恰好與活潑的氣泡及中等偏輕盈的酒體形成絕佳平衡,好似啤酒當中的橘子汽水。
|
|
|
|
場地協力:forgood 好多咖啡
音響協力:加利略藝能
活動協力:forgood live 好多聲活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