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虛的 chill,完美主義的不介意──專訪鶴 The Crane,一個 R&B 歌手的義務
2019 年 4 月 20 日,鶴 The Crane 的臉書粉絲專頁發文,睽違三年的新消息卻是樂團即將結束。從此鶴送走了團員,卻沒有送走「鶴 The Crane」的名字。
「今後,『鶴』真正的成為一人單位。我是鶴,是歌者、彈奏者、也是製作人。」
在鶴 The Crane 之前,樂團名字曾經叫林泰羽,用的是他的本名。每當樂團比賽或表演時,那個名叫林泰羽的人站在舞台中央說,「大家好,『我們是』林泰羽。」講起來有點奇怪,有時自己也嘴軟。
用自己的名字站到樂團最前面,本來也不是他的意思。高中參加成功音創,社團裡大家都想學樂器,本來想當鼓手的鶴被推去當主唱,一唱就是兩年。上了大學之後,同一批高中好友繼續玩樂團,團員之間的共識是,這個團就是以他為主、唱他寫的歌,其他人自動往後退。就連報名比賽都用他的名字,只是當一群人一起上台,大家自然都成了「林泰羽」。
後來樂團林泰羽贏了幾個音樂比賽、跑過幾次演出,他們才意識到是時候該有個認真的團名。苦惱的師大夜市旁公園,好友王建權天外飛來靈光說,那就叫鶴吧。
那就叫鶴吧——三年之後他對自己說了一樣的話。
彼時樂團鶴 The Crane 已經休團一段時間,團員們有的出國念書,有的進入職場,聚在一起表演成了困難的事,只有他下定決心還要玩音樂,即使只有自己。他把決定告訴樂團,團員開玩笑說像是被遣散,順便把鶴 The Crane 的名字當作祝福留給他。
他覺得這樣很好,「因為我想不到更好的名字。」

成為一個 R&B 歌手
即使當時在音樂圈,「林泰羽」這個名字甚至比鶴來得響亮——大學畢業之後,他先用本名當起鄭宜農和 HUSH 的樂手班底,之後更成了鄭宜農重要的音樂夥伴,不僅擔任歌曲製作人,兩人甚至共同創作了電視劇《奇蹟的女兒》《鏡子森林》的配樂。
鄭宜農曾在一篇文章裡側寫他對製作人鶴的觀察:
「一週後,這傢伙陸陸續續丟了幾段音樂來,我點開一聽,整個嚇壞了。在我做的片段裡,他可以說是抽取所有旋律重點以後,完全換掉音色、並以新的和弦進行鋪底,其中最令我驚訝的是『細節』的誕生,不難想像每一段配樂的分軌數應該都是我原本的兩倍以上,小提琴拉一聲是一個音色,一個音色又掛上不同的 plug in 變成兩種音色。讓我們來想像他腦袋裡的樹狀圖,從一個音開始生長蔓延,到最後變成一座森林的過程,這是需要怎樣的強迫症,怎樣鑽牛角尖的性格,才能誕生這樣一小段『半成品』,秒數甚至不超過一分鐘。」
對細節的專注,讓鶴成為如今音樂圈裡讓人信賴的名字。除了被他奉為恩人的鄭宜農,之後唱爵士香頌的彭佳慧、電氣民謠的凹與山,甚至拉古典小提琴的盧思蒨,都找上他製作音樂,因為他願意認真對待每個細節。
朋友形容他,是那種做每件事情之前都會想出一番道理的人。他也覺得:「某種程度上,我做的每件事情都要有一個它要完成的目的,我會想為什麼要這麼做、這麼做能不能達到我想要達到的目標。」
2019 年送走團員再出發時,鶴已經想得徹底,從音樂到自己的樣子都是。
那一年和鶴 2.0 同時誕生的是新單曲〈Monday Girl〉,曾經寫 indie pop 的樂團主唱開始唱起 R&B,對他來說像是校正回歸。
「其實在玩團後半段的時候,我還有身邊大部份的人,聆聽的習慣已經開始轉向 R&B,或是 Urban 和 Hip Hop,像是當時的 Tom Misch、Daniel Caesar、Childish Gambino 這些歌手。」
然而當時他自己寫的歌,不管是樂團鶴的 indie pop,或是另一個樂團他者的電子民謠,都還沒跟上這些耳機裡的聲音。「好像平常走在路上在聽、在吸收的都是這些音樂,可是我們還是在做以前我們曾經喜歡,或是我們擅長做的東西。所以會一直有一種跟不上的感覺。」

直到〈Monday Girl〉和〈LIMO〉推出,接連收穫了過去不曾有過的熱烈迴響,他終於有了心口合一的暢通感。接下來,要打通的則是視覺與聽感之間的統一。
「我覺得不論是什麼曲風,大家都會期待歌手要有某一種呈現的狀態。那是一種義務感。」
他畢竟無法想像用最宅的樣子唱最時髦的歌——為了成為 R&B 歌手,他要時髦、要 chill、要優雅又有一些招搖,要用點力又不能太用力。
在做〈Monday Girl〉的單曲封面時,鶴丟給設計師唯一一個要求:「我想要這東西看起來很 R&B 的樣子。」如果不多解釋,那段時間他和設計師的對話簡直像在通靈。「我會跟設計師說,這東西看起來很 R&B、這東西看起來不 R&B——有些顏色看起來就是很不 R&B,你看到你就知道。」
R&B 作為一種視覺形容詞,不只仰賴當下的直覺。那段時間他研究了所有唱類似曲風的人,從顏色調性到拍攝主題、穿著打扮,他順著歸納法的路線走到底,有一個清晰的人物形象在那裡。
他要成為一個看起來很 R&B 的歌手。
我想要的樣子
但是歌手如何 R&B?每一次鶴回過頭檢視演出的影片,常常覺得舞台上的自己,很不帥、很不 chill、很不 R&B。畢竟一開始的他,甚至沒有想要把自己定義為歌手。
「因為最初其實沒有用歌手或藝人來想像自己,我也不希望大家先入為主地認識我的名字或樣子。我希望大家理解這是一個一人樂團,對我來說這樣比較能夠把自己放在後面,把作品擺在前面。」
好在穿起 R&B 歌手的裝扮,過程倒是不需要經過適應期。「我常常在想,可能是我自己從小的個性本來就比較愛漂亮,所以其實在設定這個形象的過程中,我是很享受的。我一直都想做這些事情,剛好現在有個機會。」
機會一來,他順理成章地穿起西裝大衣、塗上青蘋果色的指甲油,甚至揹起羽毛翅膀,自己玩得比誰都開心。
在如今不以造星為唯一出路的華語樂壇,他的樣子站出來,看起來就像個不折不扣的明星——只是模樣和從前反差過大,後來的歌迷回過頭考古 2019 年之前的鶴,翻出那些被他歸類為黑歷史的影片,看著曾經黑衣素顏的他,一邊在留言驚嘆「畫風突變ㄉ泰羽」。
2021 年簽進新樂園廠牌之後,公司讓他照著原本的形象繼續玩,只有經紀人跟他隨口一提,「我覺得你頭髮可以留長。」
後來他不只留長還燙捲,效果意外地好,一頭中長捲髮從此成了鶴的名片。長髮意想不到的附加好處是,即使只穿一件白 T-shirt,看過去就已經像個 R&B 歌手,更像個明星。
「以前我會覺得這些事情是次要的,它應該放在音樂後面,所以我怎麼樣打扮,只要還在一個幅度內就 OK。但是慢慢發現,這些事其實是對於整個事業體是有幫助的,而且它不會影響到創作上的本質,它就好像在幫音樂增幅,讓更多人可以被吸引進來。」

連站上舞台的姿態也是。以前樂團表演大多配著 keyboard 自彈自唱,肢體被框限在樂器周邊 30 公分的距離,如今結界破除,他反而不確定一個 R&B 歌手該怎麼在舞台上動作。
去年夏天他參加台南漁光島的春浪音樂節,那是他第一次的戶外演出。表演是在白天,但站上舞台後海風狂吹,一站到逆風方向,立刻吃了滿嘴頭髮。
當下他立刻就心虛了。「一下子就失去肢體的流暢性,因為要一直撥頭髮,很不帥。我本來就已經不是一個在肢體上很放鬆的人,這種情況會讓我很沒自信,然後大家又一直拍!」
更多時候,不帥無關風量或風向,純粹是他在看影片檢討時發現,自己總是走太快。
「在表演的時候,主觀視角會覺得旁邊速度很慢,所以常常在走動或做動作時都太快了。其實有時候你只需要在同一個地方,完全不動地站好四個小節,之後再開始動,那個表演的張力落差就會拉出來。」
他甚至為此去上肢體開發的課程,找到每一種旋律適合的律動方式。曾經玩樂團、做幕後時的他覺得這些都是與音樂無關的事,然而成為歌手之後,才知道這每一件事都和音樂有關。
「我不是為了要讓自己更像一個明星,或讓表演看起來更精彩。我的目標是為了要讓我自己呈現出來的樣子,跟我想要呈現的樣子最像。當我在舞台上能夠做到和想要的一樣,我就會有自信,有自信我就可以把表演做得很好。」
多出來的 3 公分
剛開始學著面對媒體的時候,聊起曾經因為甲狀腺腫瘤開刀的往事,他開玩笑說自己騙朋友這是自殺未遂的疤痕,現場笑成一片。「可是新聞出來的標題可能就變成 『男星自殺未遂』,然後文章裡面才會解釋這是個玩笑。」
熱愛垃圾話的他第一次遇到這種挑戰。
又或者某一天他突然發現自己的名字多了一個響亮的前綴抬頭:「身高 185,多益 935」。抬頭甚至還押韻。是為了跟 935 湊韻腳嗎?「因為我其實是 182。」
他一直都在消化這憑空生出來的 3 公分——甚至在這個 slogan 出現之前,他都從來沒有認知到「長得很高」原來是一個外貌的加分題,從此拍照時要特別注意,得拍得高。就連多益成績他也沒覺得有什麼好大驚小怪。「我是真實地、百分之百地覺得,935 其實不是什麼太驚人的數字⋯⋯。」
為了音樂,他樂意穿上日常不會嘗試的、可以一遍又一遍琢磨自己在舞台上的姿態,只因為那些都是和音樂有關的事。而真正需要用力習慣的,還是這些在音樂之外的毛邊小事。
但也就因為這句 slogan,去年鶴發行〈PRINCESS〉單曲時,多益台灣官方粉絲團竟然幫忙宣傳新作品的消息,感激之外他依舊難以適應。「我不知道⋯⋯我真的不解⋯⋯。」
因為身高或多益成績而來的聽眾,和他自己作為聽眾的習慣實在距離太過遙遠,但作為藝人和歌手,理解是他該做的事。
「在這一波宣傳之後,我才發現原來世界上有很多人吸收資訊的方式是這樣的,我開始同理他們後,才慢慢消化掉我自己的那種尷尬。畢竟我總是希望音樂這件事情被擺在最前面,只要和音樂有關,都會比這些隱私的事情來得舒服。」
但舒服與否,永遠是只關於自己的課題。「我覺得調適完之後,我比較能夠接受,其實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是一個跟人拉近距離的方式吧。」
他像看自己的表演影片那樣,新聞或訪問刊出後再撿回來複習,為的不是檢視自己被如何呈現,而是拆解內容的生成過程,並不是問題與答案的單行道,甚至大部份時候對方想要的,只是一個可以寫下來的內容。
金曲入圍名單公佈後,媒體問他得獎的話會不會在台上求婚,他卻繞了個彎,說起和女朋友一起叫了一千元外送當慶祝的事。「所以有時候不見得是你一定要回答或不回答問題,而是你知道怎麼樣跟人互動,讓彼此都覺得,我們今天的訪問已經夠了。」
於是他才發現,182 和 185 之間落差的 3 公分,是那些與音樂無關的事的高度。而有時那 3 公分反而最讓人印象深刻。
他一直記得一個 YouTube 留言:「那個人說我長得很像聖結石跟哈利波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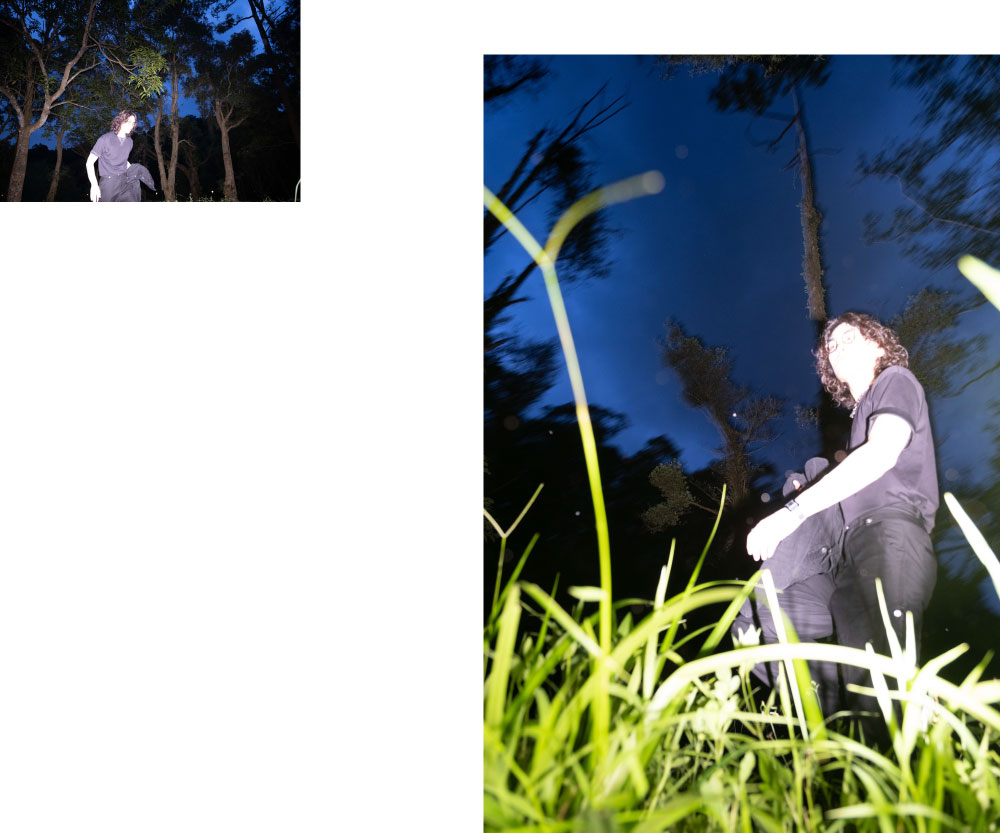
就是完美主義者
到現在鶴幾乎已經接受,自己身上歌手和明星的標籤大過於音樂人身份這件事。但下了舞台、回到錄音室戴起髮箍,他還是習慣當個製作人,聊起音樂一秒從明星歌手切換成技術宅。
最初生起製作人的意識,是他開始唱歌的時候。「因為我覺得我不是一個簡單錄個 demo,在家吉他彈一彈,就能讓大家很有共鳴的那種人。所以我需要知道那些我喜歡的東西,怎麼能夠跟大家的共鳴取得最大的交集。」
後來他發現那些交集,都在最細節的地方發生,做音樂時是一顆音符、一種音色,當明星時可能只是一串珍珠項鍊。最小的地方,越難以忽略,也越讓他感興趣。
完美主義——他想起這個許多訪問裡被重複提及的字眼,一開始他不覺得那是自己。「我後來認知到,那個感覺不是說我一定要把東西做到最好,那會變成一個匠人。反而比較像是我持續在一個很心虛的狀態,一直覺得這個東西哪裡還不夠。」
鄭宜農以「鑽牛角尖」形容的《奇蹟的女兒》配樂經驗,也是來自心虛。「每一個階段我都會一直聽一直想,然後跟我自己喜歡的作品相比較——哇我還差那麼一大截。所以我會一直在一個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很慌張的情況下,發現自己還不夠強,然後不斷補強。」
他始終覺得完美主義不算是個正面的詞,直到今年他才願意接受,好吧,這就是完美主義。
承認完美主義,是他發現自己被絆住了。去年在錄專輯最後一首歌〈Up In The Clouds〉時,他才剛確診康復,唱不到半個小時聲音就啞了,只要錄到有一句還算能用,就得趕快往下一句前進,結果整首歌都留下坑坑疤疤的遺憾。到最後還是製作人海大富告訴他,「 A 跟 B 這兩種選項,其實沒有差那麼多。」意思是請他放過自己。
是時候放過自己了嗎?
首張專輯《TALENT》發行時,他在 Instagram 為作品寫下註解:
「創作的每個當下都在選擇,每個構想一開始都只有 65 分,我一直走一直走、用時間探索所有可能,始終等不到更好的答案;直到死線前的最後一刻,才驚覺自己之所以止步不前,是因為一開始的答案就是 100 分,只是當時的我沒有信心。」
那樣的彎彎繞繞,也是創作者和表演者都必須經過的儀式。心虛是一輩子的包袱,他只能盡量做到在舞台上的時候,讓一切雲淡風輕,儘管台下的他用盡 100 分的力氣做音樂,當明星。
——畢竟他還在學著成為一個 R&B 歌手,要 chill,要鬆,要看起來不介意。

▍〈鶴(之景觀渡假莊)園〉
時間|2023/08/06 (日) 20:00
地點|Legacy Taipei 音樂展演空間
售票連結|https://www.indievox.com/activity/detail/23_iv024392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