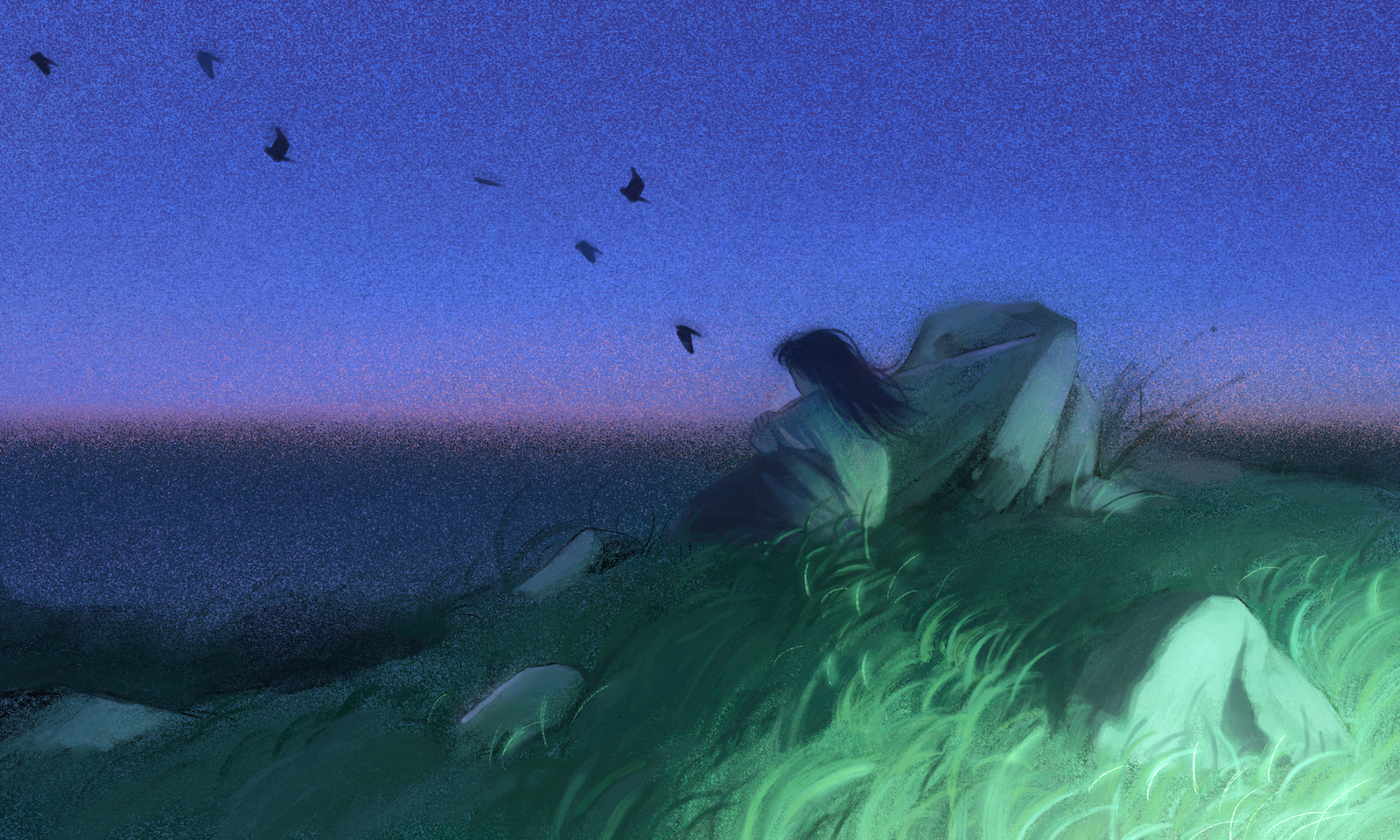
布魯塞爾的雨下得跟台北一模一樣──專訪林禹瑄,詩和遠方的告別式
26 歲,布魯塞爾機場,林禹瑄一無所有。
20 小時前她在台北,剛把大同區的套房清空。「那時候我把一袋衣服先放在樓下,然後去樓上搬比較大型的行李下來,下來的時候,那整袋衣服就不見了。」大概是被偷了吧。為了趕飛機,無暇處理,匆匆去往機場,順利在平流層度過 16 小時。沒想到抵達比利時,履帶上空空如也,另一個行李也不見了。
身上剩小背包。幸好錢包跟護照還在。
「我想說,好啦,我是想要一個新生活。但這也新得太徹底了。」
朋友說她瘋,怎麼真有人一張機票說走就走?大學每年暑假去不同國家打工換宿,她是不會事先規劃的那派,「那時候還沒有智慧型手機,機票要印出來、還要用紙地圖⋯⋯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活下來的。」
柏林。蒙巴薩。史普利特。明尼蘇達。葉里溫。貝爾格勒。奧斯陸。去過的地方被她寫進詩與散文,翻譯詞彙有異國的性感。而今她定居布魯塞爾,距離老家台南一萬多公里。詩和遠方——出自 2011 年高曉松寫給許巍,勉勵人不苟且於生活的雞湯歌詞,對林禹瑄來說是日常。
可她仍是苟且的。
去遠方,人們眼裡追夢與實踐的體現,一開始,只是為了逃。
台南
遠方的反義詞是家。從小長大的新營被她稱之沙漠,「沒有電影院,也沒有百貨公司(雖然我不喜歡百貨公司),書店很少,以前只有一間金石堂。」
林禹瑄一直想離開。小時候媽媽在餐桌上告訴她,女生拿筷子,拿得近就嫁得近,拿得遠就嫁得遠,她二話不說握住了筷子頂端。
想離開的,是家,卻不只是家。高一分組時,她擅自填了社會組,給不太管自己的爸爸簽名,「那個暑假我媽就非常地抓狂。每一天都會說,唸社會組到底要幹什麼、興趣不能當飯吃啊。」兩個月她就屈服,回去唸自然組。
「可是,尤其是物理,我非常痛恨物理。」讀理組很痛苦,做不喜歡的事很痛苦,但太會考試了,她甚至沒有不痛苦的資格,「我也沒有勇氣擺爛,因為我人生前 25 年就是非常努力想要滿足媽媽的期待。我只覺得很不開心、很不開心⋯⋯」
之所以想離家,或許正是長期被母親威權壓制後的反撲。「會不會聽起來有點重?但是家對我來講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也導致後來我去很多地方,都不會有家的感覺,因為我不知道『家的感覺』是什麼。」
學校也不安全。高中被籬笆與鐵絲網圍起,夜晚與假日都被褫奪,比起同儕更多是競爭關係,升學主義的輾壓裡,唯一能讓她撐開自己的,是喜菡文學網。
1998 年創立的古早文學網站,頁面如櫥窗般分層,不同子區塊,提供創作者練習、投稿、競技,「我就會在上面發東西,那時候如果你的詩寫得夠好,版主就會把你放置頂。當時我就只是想:我一定要被置頂。我就覺得我一定要。」
她也投文學獎,拼命寫,計算每一個文學獎的公佈日、倒數編輯什麼時候打電話。17 歲那年她得了全國學生文學獎,典禮上遇到彼時《聯合報》副刊主任陳義芝,「他偷偷跟我說,欸,妳得首獎喔。」
獎金規模更大的,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的新詩首獎。
整個下午只剩我們並肩
蹲在這裡,吃同一顆梨
讀同一首十行的詩但沒人開口
你將果皮削成了時間,盤在腳邊很薄
很小心一如你的呼吸——〈那些我們名之為島的〉
真的滿開心的,她說,「如果把我的寫作生涯畫成一個折線圖,那可能就是最高點。」有獎金,有獎座,目光跟燈光在她身上,「那時候我在意這些勝過作品本身。」現在想來,讓自己在成績單以外的地方置頂,或許是她對家庭、學校與原本生活的叛逃。
連兩年得獎,她上過兩次副刊。然而高三另一度上《聯合報》卻在不同的版位:今年大學學測的滿級分考生中,有兩名考生的嗜好都是閱讀聯合報。他們分別是嘉義縣協同中學的沈昕慶和台南縣私立興國中學的林禹瑄。
報導裡提起文學獎,充其量是滿級分光環的點綴。閱讀與寫作始於逃離課業,最後卻又關乎分數。本以為透過文學離開了什麼,結果還是在原地。
〈那些我們名之為島的〉後來被選入多本詩選,成為標誌台灣七年級詩人的一道戳記,許多人訝異,如此洗鍊的筆風竟出自 17 歲少女之手。可是誰在乎。
「我們寫東西的人覺得很重要、很了不起的東西,對文學圈外的人來說,是沒辦法衡量的。我沒辦法想像我媽跟其他人說她女兒在寫詩。」出了文學圈,滿滿獎狀不過是一疊紙,母親沒有因此同意她讀想讀的。勉強自己填台大牙醫,仍被說可惜,「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會跟你說,明明分數有到,為什麼不選醫學系?」
台北
「我那時候的想法是:讀醫學系要達到自由之身,必須經過 7 年,還要再加上住院醫師 5 年,太久了。但牙醫系 6 年就可以出去工作。」反正都會痛苦,少一年算一年。至少她如願離開了家,來到曾經心中的遠方,台北。
「遠方就是一個,什麼事情都在發生的地方。你會覺得那就是台北。至少有百貨公司跟電影院。」
真正到了台北,讀牙醫,她適應又不適應:「唸牙醫的時候,我把會考試的才華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很會瞬間記憶法。同學可能考試前一兩個禮拜就開始唸書,但我前一晚開始唸,隔天都會答對。不過考完就全都忘記了。」一切不變,一切又只是高中的延續。
但不同於高中,她與文學的關係變了。
大學期間林禹瑄出了兩本書。當時有許赫發起、針對未滿 19 歲詩人舉辦的 X19文學獎,她拿下第 3 屆首獎,獲得出書資格,隔年於是有了《那些我們名之為島的》,14 年後的現在是二手書市裡喊價到上千的絕版品。
隨後她申請到國藝會補助,得時報文學獎同年的 23 歲出版了第二本詩集《夜光拼圖》,陳芳明在推薦序裡說:「她是我所認識最年輕也最早慧的詩人。」
那幾年開始有人叫她才女。她不相信。
別人都說她起飛得早,但在她看來,自己才是落後的那個。
在文學獎裡遇過、看過的同輩,紛紛躋身人文科系,有的耕耘創作,有的浸淫學術,只有她每天面對的是鐵質的術語,鑷子與口鏡,「他們都能滔滔不絕講什麼東西出來,我就沒辦法,我也沒有時間讀這些東西,很挫折。」
只剩牙醫系學長向別人介紹她時冒出一句:「她有在寫詩。」對方通常也不知道怎麼回應。
然而所有人都起飛了
只剩他在原地
踱步、眨眼、點打火機
繼續誠誠懇懇地呼吸
「什麼也沒有變好。」——〈所有人都起飛了只剩他在原地〉
文學窄得不足以容身,牙醫生活也更逼仄。學校裡幾年還能撐過去,但畢業後進入職場,下刀的地方從模型換成活生生的口腔,不允許僥倖,一陣戰慄瀕臨:「你要對你的病人負責。不能說因為是考試所以擺爛。有時候病人太相信我,但我技術沒有很好,我其實滿愧疚的。」
甚至她不懂該怎麼訴說這份痛苦:「外面的眼光看起來,我就是走在一個非常光明的軌道上。那時候我有一個男友,他也是牙醫,我媽很喜歡他。周遭人的感覺就是,喔那你可以去結婚了。」
「但只要想到後面十年,都是照這個劇本走,我就非常絕望。」
當時新聞報導台中一位女牙醫,結婚不久跳樓。「那好像非常有可能就是我。」那則新聞剪影了社會對「成功者」的刻板與不解,「大家就會說,啊她工作這麼好、然後又剛結婚,怎麼會。怎麼會想要跳樓自殺?不是很成功的人生嗎?」
機場
「如果我繼續當牙醫的話,寫作大概就會死了。」某天下班回租屋處的路上,她才發現,10 年,整整 10 年,她都做著自己不喜歡的事。「那時候,就是只想要活下去而已。我累積了很多創傷跟痛苦,卻沒有足夠的餘裕讓我難過。」
那年另一件事,是她與當時的牙醫男友分手。
會難過嗎?她只回憶最初,「我是一個滿自卑的人,他說他喜歡我,就在一起了。」
分手後,處事圓滑的前男友傳簡訊給她媽媽,大意是:非常謝謝林母之前的照顧,很可惜無法成為家人。「那是我媽很愛聽的話。明明他們才見兩次面。」知道兩人分手,媽媽開始照三餐打電話,責備她,那麼不珍惜,幹嘛不快復合。同一時間,前男友也會一天打近百通電話給她。
只是稍微偏離了劇本,好像全世界都跳出來把她拽回「正軌」——意識到這件事,她終於忍不住。要是現在不逃,以後只會更難。
她辭職了。
她清楚這意味著什麼。「就像一顆炸彈投下去,玉石俱焚。然後我就出國了。」
學過法文,她剛好也想去一個講法文的國家,好巧不巧拿到比利時打工度假的簽證,便下訂往布魯塞爾的機票。起初母親是反對的,她是非常害怕小孩不在身邊的家長,「我就跟她說我要去唸書,唸一年就回去,她可能覺得我是去 gap year。要我保證一年一定要回來。」
甚至家中向來沉默的爸爸第一次主動打給她:「我不管妳要跟妳媽講什麼,但妳只要讓她相信妳會回來就好,拜託妳。」講完就掛了。
儘管一律宣稱是去唸書,但彼時她沒有申請到任何學校,更不曉得簽證效期過了怎麼辦,去之前也對比利時一概不知,她只是想離開。越遠越好。她相信值得,「因為辭職那天真的非常開心。開心到我覺得自己很奇怪——後來才發現,哇!原來是因為在這之前,我都那麼不開心。」
她頭也不回地上了飛機。
26 歲,布魯塞爾機場,林禹瑄一無所有。
布魯塞爾
一天有長輩寫信來,語氣半是困惑半是責怪:「我都搞不清楚妳在哪裡。」我看到信後,一時不知道如何反應,因為確實也搞不清楚自己身在哪裡。那陣子常常半夜醒來,以為還睡在幼年時的房間,起身想走去廁所,卻撞上了牆,這才意識過來人在遠方。並且現實生活裡,那個幼年的房間也已經不復存在了。——〈在遠方〉
給爸媽的承諾沒有兌現,她一直沒有回去。
2015 年,5 艘載有約兩千名移民的偷渡船沉沒地中海,後稱歐洲難民危機。同一年《報導者》成立,進行記者海選,剛到比利時的林禹瑄上了,自告奮勇想做難民題,從未受過相關記者訓練的她,開始採訪、寫就〈敘利亞難民的一堂法文課〉〈10萬名無身分者的漫漫長夜〉⋯⋯
一開始本來想唸紀錄片,但在台灣萬能的牙醫學位不再靈驗,只能靠採訪經驗申請當地的新聞研究所。唸完書,又被迫面對簽證死線:維持簽證需要提供一定程度的收入證明,她開始把工作分成「會賺錢」跟「不賺錢」兩種,時間與心力成本高的報導是後者。她轉而接起了商業翻譯工作。
又離文學更遠了。
「以前會覺得,我來比利時是為了寫作。」然而在比利時,精神還沒被滋潤,生計卻先乾涸。剛到時每天都在打電話辦事,安頓好起居,她竟開始接受這樣的自己。不寫了的自己。
「有點放棄繼續寫詩或出書了。而且那時候我有理由,可以理所當然地說,反正我不在台灣、跟其他寫作者過很不一樣的生活,所以也沒有關係。落後了,也告訴自己沒差。」又是另一種逃。
好幾年,她除了日記與邀稿外,其餘什麼都沒寫。
也是那段空掉的日子,傷痕開始浮現。
她的憂鬱症加劇,有些悲傷沒有來歷,有些則像遲來的反作用力,帶她觸碰過去,「之前讀牙醫,經歷過非常壓抑自己的時光,那時候還在創傷中、沒辦法反應。所以到了國外,我就爆炸了。」
病症讓她開始記不住。那幾年的記憶幾乎荒廢,忘記臉書的帳號密碼,因此與許多人斷聯。彷彿身體自動切斷她與原本生活的連鎖。「我媽打電話來,我都不敢接,她就傳 LINE,如果 LINE 我沒回,她就寫 Email。那時候看到一個訊息跳出來我真的不敢打開,我會因為一封 Email 就卡了一個禮拜。」
她做過諮商、心理分析,釐清創傷的由來,包括為什麼媽媽那麼不想要她離開。
媽媽在傳統家庭長大,么女,上面有 6 個哥哥姊姊,「從小她被迫做很多決定,都是為了成全家人,比如她讀到高中,為了省錢就沒有繼續。」相較之下,林禹瑄對自由的渴求、不必犧牲,在媽媽眼中才是不對勁,「她覺得女生該有女生的樣子。而我跟她都是女生,憑什麼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或許媽媽是嫉妒她的。
「比如說我跟她吵架,她吵不太過我,她就會說:妳就是念太多書了。」傳統觀念束縛下,媽媽認為三十歲以後最重要的就是結婚,超過一切,「她就會說,我覺得妳如果沒有結婚,或沒有小孩,那就是一事無成,做什麼都沒有意義。」
「我要怎麼樣才可以讓她理解這些事情造成我的困擾?」她不願過多苛責同被時代掐著的母親,只是突然知道自己沒有辦法。「她覺得她經過的痛苦比我還多,所以我的痛苦對她來講就不算痛苦。」
我住在母親一生漫長漫長的傷口裡
無法開口,無法不感到疼痛——〈春天不在春天街〉
如今母女已經兩年多沒有通話。期間還是有悄悄回台灣,但寧可睡青旅,也不想回家。畢竟隨著父母在她出國後搬進透天厝,原本的家也真的不在了。
「沒想到現在,家反而變成遠方。」
.png)
斯雷布尼查,蒙巴薩
定居布魯塞爾後,像要報復過去的生活般,一直起飛,一直降落,尋找新的遠方。比如她鍾情巴爾幹半島,內戰史喧騰的歐洲軍火庫。「當地作家會形容自己國家:來自這裡的人,眼睛裡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憂傷。」
她去那裡找眼睛。
1995 年,波士尼亞東部小鎮的「斯雷布尼查大屠殺」,8 千多名穆斯林男子在數夜間被塞爾維亞軍隊殺害,多名婦女與孩童遭性侵,二戰後歐洲最大規模的種族滅絕。爆發時小鎮居民遁逃的林中路線,紀念日人們會重新步行,用身體復述歷史的痛。21 年後林禹瑄也踏足,遇見一群內戰時期參戰的老兵,有人眼睛被炸出窟窿,有人展示頭上手榴彈造成的開裂,組織液流出。
「有個老兵會講一點英文,我說我有在寫報導,他就一直叫我 CNN,還跑去跟人家說『這是 CNN 的記者!你要跟她講所有事情。』」於是她聽到很多故事。「他們到現在還是彼此仇恨。在波士尼亞,遇到當地很多穆斯林,都跟你說塞爾維亞人就是很壞。塞爾維亞的角色有點像中國,會覺得南斯拉夫人皆兄弟,其他人就會跟他說:我們才不是。」
去年她也走訪塞爾維亞,遇見一個音樂家,「他跟我介紹他們國家的音樂,把地圖拿出來,他指著科索沃說『這個科索沃區』。」然而當時科索沃已經獨立。「我不覺得他講這些有惡意、或他想用暴力統治其他民族。他給我的感覺就是:我是南斯拉夫人,我只是很認同我的國家。」
混亂的歷史與邊界、轉型正義、強國以民族主義之名凌弱,她竟在別人的眼睛裡,看見自己故鄉的身影。
類似的機遇很多。尤其以台灣人的身份穿行,難免被側目。「比如說有時候我遇到伊朗人,伊朗人就會跟我說,你知道像我們這種國家的人⋯⋯」那是一種先於語言與貨幣、流通在國際的憂傷。
肯亞同樣令她依戀。那時她把布魯塞爾的公寓清空,成為沒有地址的人,去肯亞馬庫由的寄宿學校當志工。學校由一個肯亞人、一個美國人創建,支援家裡沒有通電、食糧匱乏的孩童,提供暫時的家屋,讓他們可以吃、可以睡、可以寫作業。
令她沒想到的是,跟她一樣,小村居民也有心繫的遠方,「我在村子裡遇到的人一輩子沒去過蒙巴薩,但會不斷跟你說那個地方有多好,有大海。有天一定要去蒙巴薩。」學校警衛常開玩笑,星期天,他會穿上唯一的白襯衫、西裝褲去教會。「我問他去哪,他會說,去蒙巴薩。」
星期天你到蒙巴薩
帶上最堅硬的箱子
裝滿破碎的手錶
走在形狀尖銳的路上
感覺安全、完整
而重新有了願望
你反覆立好衣領,反覆
唱一首輕快的歌:
世界越冷漠、殘忍
你越快樂——〈星期天你到蒙巴薩〉
「我很喜歡在小村子的生活,很樸實——這樣講很傲慢吧。我知道這對他們來講一點都不好玩,可是在那裡,早上 7 點起床,晚上 8 點睡覺,沒有網路,用井打水,用手洗衣服⋯⋯」原本她會因為一天沒有上網就產生脫隊的焦慮,「但過了沒有網路的兩個月,回台灣連上網,原來也沒有錯過什麼。沒有什麼真的重要。」
沒有什麼真的重要。也沒有什麼遠方非去不可。
近年她很少遠行了,因為要背負的越來越多。春天街的日子,她談了一場戀愛,分手,養了貓,漸漸熟稔布魯塞爾的雪與啤酒。採訪時請她在家中轉一圈:灶台上累積空瓶,盆栽與玻璃窗對坐,室外有花園、旋轉梯,傾斜的陽光。
「已經沒有特別想去毀滅式的流浪了。當然還是會想,去哪個地方感覺很快樂,但每次去完好像也沒有多快樂。」
以前覺得年齡不成問題,現在也稍微在意。流浪塞爾維亞,打工換宿其他人都二十出頭,當她說自己三十了,便被驚訝的眼神淹沒,「好像有點太老⋯⋯是不是不應該再任性地亂流浪?但可能還是會啦。」
「其實去流浪,就只去躲問題躲一兩個月,回來之後,問題還可能更大。就是製造新的問題來解決前面的問題。」
周折在沒有盡頭的疆域與國界之間,她終於發現,遠方,始終是一個相對詞,是海子所說:「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
追尋遠方,成真,然後幻滅。什麼也沒有發生。
春天街
她其實沒有想過要再出詩集。
28 歲收到的信裡,讀者告訴她:「有個女孩也讀妳的詩,後來她離開了。」那封信並非責備,但她卡住了,也問過自己:「要販賣悲傷到什麼時候?」
3 年前,她忽然覺得夠了,「我在比利時已經經歷滿多輪迴。我不知道人生要怎麼辦,完全偏離正常的軌道,也沒有任何參考,好像在外太空飄浮一樣。」讀書、工作、出國,什麼都做了,又好像什麼都沒做,幾年前本想專心寫點東西,申請國藝會補助,也無果。
「你覺得,江郎知道自己才盡嗎?」她說她開始害怕,為什麼人們只記得江郎的才盡,卻不記得他的作品?他真的有才嗎?飛得夠久了,她想找一個合適的降落點:「我想要知道才華什麼時候用完,什麼時候該收手。」
「既然沒有要出書、寫作、生小孩,原本我的人生計畫是,我要寫一本小說,35 歲就可以走了。」
直到去年 2 月,編輯達瑞寄信來問,想不想出詩集?「我想說,出詩集,你確定?哪來的錢?但他說他很想。」揣著不安、心虛還有一點願望,最後她答應了。
距離上一本書 11 年,今年 3 月《春天不在春天街》出版,她是被記得的。詩生活發文「讀者心目中最期待的詩人林禹瑄終於出書了」;詩人唐捐臉書上寫「傳奇的抒情詩人再出發」;把她的名字打入搜尋引擎,社群上可以找到不少「終於」開頭的句子。
終於。林禹瑄終於。
詩集編寫期間,她又覺得自己好像好像好像——好像可以寫下去。不見得是詩,「散文我會繼續寫,之後可能會想寫小說。寫得好不好還不知道。」今年要 35 了,她練習養成規律,週一到週五是工作時間,週末如果沒有跟朋友喝酒,就交給寫作。從生活回到生活,曾有的遁逃與流浪並不徒然:位移是 0,卻拉出了纏繞半個地球的路徑長。而文學從來更關心後者。
春天街,雨什麼時候下下來,她自己知道。
《春天不在春天街》
作者|林禹瑄
出版|二十張出版
出版日期|2024.03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