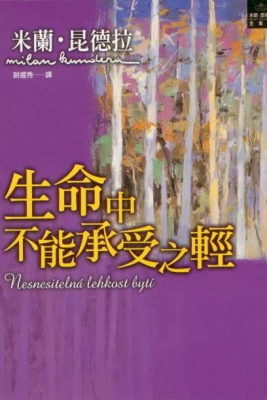愛情常態|當我向你關上我自己——艾莉絲.羅爾瓦雀《蜂蜜之夏》
從一處很小很小的開口,淨透的金黃色蜂蜜,滴流下來。就像這世界一處很小很小的開口,文明流向荒野,浸透一個養蜂人家的質樸和草莽,侵蝕他們的傳統產業和家庭秩序。就像女孩敞開一處很小很小的開口,含住的蜜蜂,爬出洞口。乾淨純粹的情意,滴流下來。
男孩來到之前,女孩從來沒有想過遮掩,遮掩自己的情緒。並非無從遮掩,而是無須遮掩。她從不害怕袒露自己的懶惰、憤怒、直率、快樂。她不害怕被看見。圍繞她的,只有家人。她一直順著生活的波動,無可無不可地,承擔家中的勞動。不曾退出生活,也就不曾退出自己。
男孩來了。她變得沉靜,羞怯,彆扭。他們沒有語言可以交談。不用語言,就可以交談。電影常常獨拍女孩,若有似無的表情,望向某處,然後低下頭來。接續的鏡頭,獨拍男孩若有似無的轉頭,看向某處。鏡頭成了一個開口,留下一個空缺的眼神。眼神的終點,在鏡頭之外。沒有事件發生,那眼神投擲的空缺處,就是唯一的事件。
男孩來到女孩面前。她雙手摀臉,張開,露出臉頰。她微啟雙唇,任口中的蜜蜂緩緩爬出,爬上臉頰。最危險的,就在近處。最遙遠的,已來到面前。他們相視而笑。偶爾,他們聚在一起,刮除蜂箱的蜂膠,將滴流的蜂蜜裝罐。父親不在的時候,女孩的妹妹一如以往,跳起舞來。她對姊姊發笑,等姊姊一如以往地,哼唱出她們的歌曲。可是女孩動也不動。她和妹妹之間,隔著男孩。她無法隔絕男孩的目光,落在妹妹的身體上頭。她咆嘯起來。
她咆嘯,因為忌妒,且因自己的無助無能。對於袒露的一種否定,也是對於自然的一種否定。恐懼自己的真實遭到否定於是就先自我否定。需要神秘。需要假面。需要空白橫亙在兩人之間。因為懸宕的曖昧是唯一繫緊彼此的方式。不去下賭。忍受未明。唯一的把握,就是不去把握。以孤傲來掩飾脆弱。一動不動迎來距離。所有冷漠都是為了保持親密。避免結束,避免破曉,就讓自己成為謎,成為神秘。如同那些流淌在地上的蜂蜜,黏稠地趨向僵死的狀態。女孩的情感晶瑩,醇厚,不再流向他方。情願停滯在此時此地,依附此時此地。
一切關乎展示。她不扭動,她收斂身體,張開嘴巴,任危險和禁忌爬過。僅僅想要,展示內在的靜定,而不是外在的線條。就像這部電影的詩意不來自於單一畫面的視覺美感,而是錯過的眼神、蕪雜的生活如何透過剪接而連繫起來,揭示內在生命的矛盾和豐饒。我們和女孩一樣,從來不知道,自己的身體是一座開口,直到我們渴望親近另一個人,再近一些,直到能夠生吞他,讓他毫髮無傷地,活在自己裡邊,留守他的純真和孤獨。結局,男孩和女孩取暖的洞穴是一個開口,空無一人的房門布簾也是一個開口,原來,最深沉的信任通向彼此,最輕盈的包容穿透彼此。當我向你關上我自己,才知道你我敞開的我們,那樣深邃,那樣遼闊。每一個此時此地,都是奇蹟。
【愛情常態】
我不知道愛情如果不是最暴力、最羞恥、最甜蜜的勒索,它還能是什麼?
這些是我在文學、電影、戲劇、舞蹈、繪畫、音樂裡所理解到的愛情常態。
【吳俞萱】
寫詩、影評,策劃影展與讀書會。
著有詩集《交換愛人的肋骨》,電影文集《隨地腐朽──小影迷的99封情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