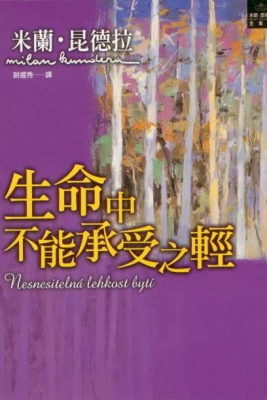愛情常態|《魔物戀人》的愛情神話學
殘暴的愛無止歇地纏繞著我,
直到它以利劍、以荊棘刺穿我,
在我心中開出一條焦灼的路。──聶魯達
沒有一對愛侶不是末世的族類,相互餵養相互侵吞。末世感寫就了愛情的基調:我們相信只此一次,我們獻出所有,最強的火焰、最貞定的心。沒有犧牲可言,因為我們的個體性融入了對方的個體性,我們無法不成全對方,畢竟那也是我們自己。權力相生相剋,我們之所以在某方面退讓,必定在另一方面馳騁,無論外人看待這一段愛情如何負重歪斜,都是我們自己平衡出來的。這是一種相對的平等,一種猶疑不定的倫理秩序。
沒有對峙,便無法共謀。真正的族類,共享一團血肉糢糊的心願和恐懼。《魔物戀人》乍看翻轉了「美女與野獸」的性別設定,描述一個男人和一頭怪物的詭異愛戀,但是,這部電影的戲劇性翻轉在於取消了真愛能夠解除封印的魔術時刻,尖刺地要我們明白,愛無法帶來超越愛的奇蹟,愛的救贖並非改變自身的形態,而是接受那一份恆常存在的異變。這不是一則頌揚愛的童話故事,而是一個認清愛的暗黑神話學。如果無法忍受荊棘刺穿,那麼,通向未來的路根本無法展開。
愛活在一種不斷自我確認的形式之中,《魔物戀人》的鏡頭因而一再穿行義大利蜿蜒蔓生的層層巷弄,越過牆面,越過塔樓,還要越過另一座牆另一座樓,無始無盡地向前穿越,抵達洶湧的海洋。即使鏡頭流動挺進一如相愛的決心,卻無時無刻不在遭逢遮蔽的視野,難以觸及那些抗拒被拒絕的秘密、抗拒被穿透的卑微。甚至在真相露出之後,男人怎麼奔逃也避免不了闖進死胡同,外在空間的迷宮巷弄和內在空間的糾結心思於是猛然疊合為一,徹底將城市景觀化為愛情神話學的發展肌理。
城市本身有了意志,呼喚愛情成形和落難。電影中多次出現在街角、暗巷、荒地的動物特寫,無論活躍的行跡或腐敗的屍身,除了對照女人身上潛藏的殘虐動物性,還催生了一股末世的氣息,吹撫那嗜血的愛欲和殘影的疑懼。一切都在朝著死亡而去,或是說,愛情的幻影非得淒厲死去,否則這一對愛侶無法面對真實的處境,無法穿越曲折無法抵達最終浪起潮落的平穩大海。
在心中開出一條焦灼的路,承接愛的溫柔和暴烈,承接愛的餵養和侵吞,這回應了原片名「春天」(Spring)的意涵。就像那首無關而同名的歌,Mia Doi Todd 唱的,打碎所有骨頭,我將重新學習走路。打碎所有骨頭,我將重新學習跳舞。這就是春天了,光禿禿的樹枝長出樹葉。我們握住一隻新的手,向微風道謝。
【愛情常態】
我不知道愛情如果不是最暴力、最羞恥、最甜蜜的勒索,它還能是什麼?
這些是我在文學、電影、戲劇、舞蹈、繪畫、音樂裡所理解到的愛情常態。
【吳俞萱】
寫詩、影評,策劃影展與讀書會。
著有詩集《交換愛人的肋骨》,電影文集《隨地腐朽──小影迷的99封情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