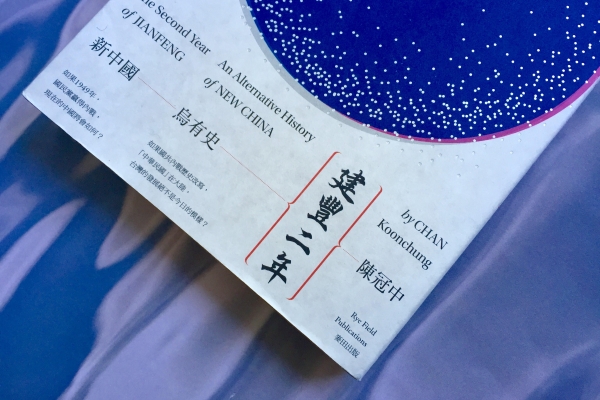這些黑暗被寫出來了
──專訪張耀升《縫》
張耀升 2003 年的出道作品《縫》新版面世,除了原本的八篇短篇小說之外,加入了四篇新作,篇章順序重新安排,「這次篇與篇之間有呼吸的感覺,緩和之後,再回到下一個悲傷的故事裡,讓情緒能相連與承接。」張耀升說。
《縫》裡有鬼魅、霸凌、自殺,苦澀的夢與秘密盤旋在不同的情節之間,某個角色在一個故事裡邪惡,卻在另一個故事裡柔軟單純。敘事與敘事之間不斷互指與推翻,在他筆下的惡世裡,沒有顯而易見的出口,沒有人可愛,也沒有人可恨。張耀升寫的故事又黑又冷,「有人跟我說我的故事應該要有溫暖,應該要有光明,讓人看了之後獲得救贖。但我想所謂溫暖的故事,只會讓人覺得弱勢者能自己找到出路,讀了這種故事反而會更冷漠。」
「而且,」張耀升說,「人們已經習慣看到弱勢者奮鬥、掙扎、找到自己的出路,如果他不奮鬥,彷彿就是錯的,這種邏輯我不能接受。」
所以在《縫》裡我們能看見:奶奶成為爸爸口中的臭老人。孩子靠著自己虛構的文章催眠自己家園是甜蜜的。中學生為了獲得第一名付出生命,為了重新開始而抓另一個人墊背。
站在我們面前的是:被霸凌而絕望的孩子、被家人遺棄的老人、回不了家探望祖母的阿兵哥、想要為祖母買一塊墓地的靈骨塔業務、買了台北房子卻失去母親老家的成功男人。
當我們回過頭來:曾被壓抑的愛情多年後反撲,這股引力是來自黑洞裡苦澀回望。故事一步一步往深處去,塌縮,再塌縮,闔上書,感覺自己全身被黑暗輾過了一回。
「寫這些,選擇這麼做,有什麼後果,遭遇到什麼批評我也都知道。」多年來,是網路上一位讀者的書評支撐著張耀升保持這種創作態度。
「那個人寫說自己有憂鬱症,他周遭的親人都禁止他看任何負面的東西。只讓他讀靜思語那類正向文章,這帶給他非常大的壓力。這個世界對他來說是一片過度曝光的慘白,慘白到讓他覺得自己非常骯髒。後來他聽說《縫》是完全沒有光明的,就去偷買來看。讀完之後他感覺自己被理解,而那種理解是光明沒辦法帶給他的。這些黑暗被寫出來了,他才終於明白自己的苦並不是因為自己的怪,原來世界上還有很多人跟他一樣。所以這本書的存在,給了他一點點安慰。這段評語十幾年來我一直記著。」

進入角色是虛構的第一步
我忍不住問了小說家,「這些故事,有幾分是是親身經歷,幾分是虛構?」
「我怎麼可能一天到晚遇到鬼?我奶奶怎麼可能在我小時候就死了,到我長大再死一次?怎麼可能?」張耀升笑著說。
「我有上過表演課。如果說編劇自己沒有表演經驗,很容易寫出難講或是不符合角色的台詞。」近年來將注意力轉向編劇和影像創作的張耀升說,「寫劇本時編劇是第一個進入角色的人,他要先演過那個角色一遍,進入角色,替角色說話,所以要有演技的基礎,我為了這件事去北藝大上了半年的表演課。」
但早在他成為編劇前,張耀升就以這種方式寫小說了。「我的小說除了少數幾篇是第一人稱,大部分都是第三人稱有限觀點。像拿著攝影機跟拍主角那樣寫,這種角度很注重角色狀態,所以在寫作時我會用演員的方式進入角色。很多人會以為我寫的是我個人的故事,其實不是,那是因為我進入了角色。」
「那在寫作上,你曾經遇過什麼難以詮釋的角色嗎?」
「有,我寫過一篇非常失敗的小說,那篇是我目前為止最大的挫折。主角是個女同志,我想了好多方式想要進入女同志的思考邏輯,可是我發現,男生看女生,跟女生看女生,就是不一樣,情感和情慾都不一樣。」張耀升曾把那篇作品拿給幾位女性讀者試讀,但她們總要讀到最後,才發現原來主角是女同志,這點讓張耀升十分挫折。「一直以來,書寫女性角色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障礙,所以我才堅持把〈鼠〉這篇放進去,因為我覺得自己這次終於突破了。」
「除了女同志之外,還有哪種角色對你來說特別艱難?」
「有有有,」張耀升說,「那種熱愛交友、應酬,覺得喝酒交際最放鬆的那種人,我沒辦法寫。我陪這樣的人應酬過,每一秒我的靈魂都在哀號。我的個性裡完完全全沒有那一面,我是很孤僻難相處的那種⋯⋯孤僻而已,沒有難相處。」
停了一會,他進一步解釋:「演技這種事是這樣的,你可以從內心找到任何一種可能性去把它放大,把它放大之後就可以飾演某種角色,可是當你的個性中完全沒有某一個面向,那個面向是零的時候,是放大不了的。其他人可以克服,可是我所學到這個演技的方法,在這裡是克服不了的。」

虛構──模糊真與假
在舊版的《縫》裡,〈洞〉是跋文,接續在〈伊卡勒斯〉之後,從排版的格式看來,張耀升本人就是故事的主人翁。〈洞〉的事件背景發生在〈伊卡勒斯〉之前,讓人分不清楚整本小說到底有幾分真,又有幾分虛構。
但在新版的《縫》裡,這篇〈洞〉就被歸入了小說之中而不是跋文。張耀升說,「新版就要告訴大家,原本的那個〈洞〉它不是真的跋文,它也是小說的一部分,它被用在擾亂讀者對故事的認識,擾亂整本小說的認知。」事隔十二年,當張耀升要讀者把〈洞〉視為虛構故事時,他就再次模糊了真實與虛構的邊界。他推翻了自己,告訴我們真跟假只是觀點的問題而已。
張耀升在《縫》中做了多次推翻,「如果你先看了〈藍色項圈〉,會覺得林友達很可惡,可是你看了〈友達〉之後會翻過來,再看〈鮮肉餅〉裡頭又有一個林友達,又再顛覆一次。為了要讓人覺得自己的認知其實只是某個觀點而已,我一再地做這種事。我希望讀者多想一點,可是有的時候我好像對讀者要求太高了⋯⋯。」
張耀升提高了語速,「面對真實事件,再把它寫成小說,寫的過程裡因為觀點受到侷限,它就一定會偏離真實,所以只要下筆,不管如何寫實,它就是假。要逼真,有時需要適度扭曲,把某個主題凸顯出來,才會比真的還要動人。這很矛盾,但這矛盾讓我覺得很有趣,我們要怎麼去扭曲真的東西,才會讓它比真的更像真的?我覺得小說創作的技術就在這裡,就是這點讓我著迷。」

一段失去同理心的日子
聊起小說集最後一篇作品〈鼠〉,張耀升說:「編輯說他一讀完原版的〈鼠〉就拉肚子。」經過一番思考,張耀升才發覺自己的敘事觀點失去了同理心。
「那個時候的我,只覺得世界的醜陋是常態,我不想美化它。是編輯指出過去的作品和那篇的差異,才讓我發現就算這個世界很醜陋,我一點都幫不上忙,但我至少可以保有同情。」張耀升說。
「為什麼會失去同理心?」
「幾年前,在我離開台中前,我曾在一個比較不適合我的地方工作。我目睹了許多不可思議的鬥爭。過去寫《縫》的時候,別人說我把人性看得很透澈,但我在那裡才發現自己根本太單純了。人性真的很可怕,大部分的人有辦法在很短的時間內自己替自己漂白,甚至說服自己是受害者,卻做出非常可怕的舉動。目睹那些,讓我覺得這個世界很殘酷,很殘忍,卻同時也覺得什麼事情發生都不意外了。但當我如此抽離地去寫這些不好的事,抱著『反正事情就是這樣』的態度時,就會變成另一種以折磨主要角色為樂的作者。」
經過了編輯的提醒,小說家才發現:「敘事者本身不能喪失同情。如果我連這點同情都沒有,我就跟那種冷漠旁觀的人沒兩樣了」。後來,張耀升將〈鼠〉從頭到尾改寫一遍,劇情相同,但更改了敘事觀點。編輯讀完告訴他:「修改後,有一種被淨化的感覺。」
「我是非常虔誠的佛教徒,是每天都會誦經和打坐的那種,」張耀升說,「對我來說這世界是五濁惡世,不是光明善良,不是期待被救贖的地方。這世界有太多讓你不如意的事,那才是比較真實的狀態。」
 |
後記
採訪結束後,我向小說家討簽名。張耀升接過書和筆,攤開封面然後說:「簽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我一般是不幫人簽的,除非是領據,也不會跟人要簽名⋯⋯」停了一下他才說,「我跟袁哲生要過簽名之後他就自殺了。當時袁哲生的寫作非常寂寞,所以我想如果去找他要簽名,會讓他開心一點,所以才跟他要⋯⋯。」他猶豫的筆尖就要碰到書本內頁時,我趕緊喊停,「不要破例,有這故事就夠了。」
小說家的筆雖然殘酷幽暗,為人卻有溫暖慈悲的一面,這才明白他為什麼要在封面上寫「黑 是最溫暖的顏色」。
《縫》

作者:張耀升
出版社:群星文化
出版日期:2016. 03.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