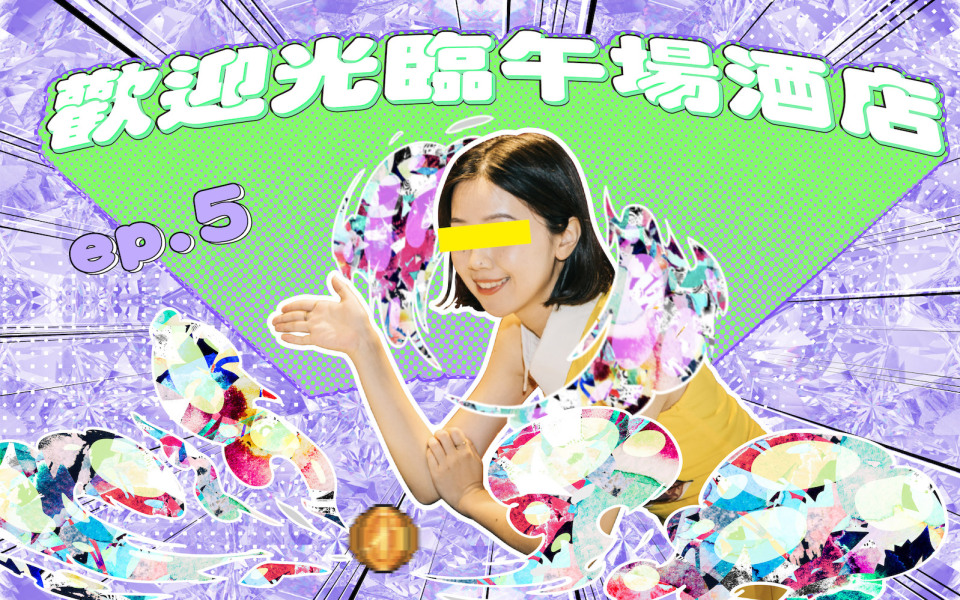
少女 A・歡迎光臨午場酒店 EP5|我是女友,還是免費的性伴侶?
鬼棲之家
法國理論家巴舍拉曾為「家」賦予一個很詩意的觀點:一切真正為人棲居的地方,都有家這個觀念的本質。記憶和想像彼此相關,相互深化。被「收容」的不只是我們的記憶,還有我們遺忘的事物。
「被『收容』的不僅是我們的記憶, 還有我們遺忘的事物。我們的靈魂是個居所。只要記得『房屋』 和『房間』,我們就學會了居住在自己裡面。」——(Bachelard, 1969)
為了離上班的地方近一點,我從板橋搬到了行天宮站。這是一棟位於街角的三層樓建築,就算是白天也不是很熱鬧的街道。房間加上廁所可能連一坪都不到,從我的房間窗戶看出去,對面是市立養老院。每天凌晨四五點左右就能聞到養老院的中央廚房廚房在準備早餐,淡淡的麻油雞香飄進房間,有時候聞得出來早餐是油飯,對於並不講究飲食的我,是一種嗅覺騷擾。
「我覺得這裡還不錯啊,妳從家裡這一條走出去就有吃的,有全家,再出去一點還有 7-11」阿昆邊滑著 google map 邊用手指筆畫著,表情興奮地好像是他要住在這裡似的。
「可是房間好小⋯⋯你真的覺得可以擺下我的書櫃嗎?還有我衣服好多,感覺大衣塞不下那個衣櫃。」說完我抬頭看著他。
「可以啦,我回去量一下,一定夠放,反正也是我來擺嘛。」他的表情看上去非常確然。伴著閒散的談話,我們邊牽手散步著去勝利百貨買一些日常用品。
阿昆果真說到做到,用不到一天的時間將我從板橋打包來的笨重箱子打理好,他把東西一樣一樣從紙箱裡拿出來,重新歸位。三個書櫃、一個貓砂盆、兩隻貓,都在阿昆有條不紊的整理節奏下被細心地組織過。
「妳的衣服我幫妳放在這喔!」阿昆指著衣櫃下的一個角落。
「什麼東西?」我伸手進去他所指之處,撈出了一袋我的酒店衣服。「好喔。」我沒有多說什麼,又把那袋洋裝放回去。
以收納的角度來說是很充份地利用空間。但那是我的職業需要穿的洋裝,怎麼搞得像要藏著掖著呢?上班族可以把明天上班要穿的襯衫整齊折好放在明顯的地方,以便隔日上班省得找時間翻找、整燙。而我呢。隔天上班前兩個小時,要從衣櫃的角落拖出那一袋洋裝,那裡面的洋裝都像酸菜一樣皺巴巴的,我必須花半小時至四十分鐘的時間把洋裝弄得平整。雖然午場不算消費高的地方,對服裝也沒嚴苛的規定,但小姐用衣著心機來吸引客人這是一定的,「不用買太貴,有變化就好。」某個小姐曾經這樣跟我說過。小姐的洋裝普遍都不是太好的材質,容易皺、起毛球,照理說應該要好好地掛起來,正大光明的掛在衣櫃裡,跟一般上班族的日常一樣。
我好奇是不是每個小姐的房間裡都有一個「隱藏的衣櫃」來放她們上班的衣服,去過幾個小姐家坐坐,還沒見過有人把去酒店穿的洋裝掛在明亮之處。
陽光薄而輕柔地照在洋裝上,彷彿若有光,一切都能合理了。
但原來,要有光是這麼奢侈的一個願望,行天宮站的家照不到光,陽光沒辦法直射到我房間,就算是正午,還是會覺得房間陰冷。若是夏天,房間有難以忍受的濕氣,也有令人苦惱,迅速蔓延的霉菌。
自從我搬進來後,跟阿昆吵架的次數就更多了,有一次,我家的兩隻貓因為空間太小,打鬧的時候有一隻不慎摔傷了前腳,我緊張地傳訊息給阿昆要他過來陪我帶貓去醫院。我很清楚記得那天是禮拜六,對常加班的阿昆來說,週末是他把待辦事項一一清除的時候,那天他安排去剪頭髮,收到訊息後他趕來我這。眼看快到他預約的時間了,我語帶生氣地問他:「你今天不能先取消陪我去嗎?yoshi 好像有點嚴重欸。」他的視線落在手機上顯示的時間,皺著眉說:「可是這個設計師很難約,而且我上禮拜就說今天要去剪頭髮了。」接著說:「妳先帶牠去看阿,而且我看好像沒妳說的那麼嚴重,不然下禮拜再去呀!」感覺到他語氣中的不耐,我急著說:「所以貓比你剪頭髮重要?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
當下也知道自己在情緒勒索,或許是對阿昆日復一日、夜復一夜、等待著他下班偶爾能夠來陪陪我的焦慮感爆發,我把悲傷全部嚎叫出來:「你現在就給我取消!打電話去取消!你太糟糕了!」我擋住門口,阻止他出去,因為吵架的時候阿昆總是扭頭就走。「我不要!我已經安排好了!」他試圖推開我。這個舉動讓我瞬間什麼都顧不得了,當下只有一個強烈的念頭:「不准離我而去。」我衝向書桌,拿起修眉刀抵在左手腕上:「你敢走我就割了!」可能我太常拿自殘威脅他了,這種勒索對阿昆已經有了抗藥性,他徑直推開門,說:「我現在沒時間搞這個,我要走了。」
唰唰。
修眉刀快速劃破我細瘦的手腕,慢慢滲出血珠,滴落在地上。後來我記得不太清楚,所有事都發生得太倉促,只記得阿昆還是走了,我們可能有在走廊上拉扯,因為回神過來,我蹲在走廊的樓梯上用紙巾擦拭滴在樓梯上乾涸的血。
隔天上班的時候,John 用抽菸的名義,把我叫到一個包廂裡,我也知道他要講什麼,我兩腿併攏,深呼吸,準備接受他的拷問。
「又來了啊,這次是怎樣?跟男友吵架喔?」我覺得一陣難堪,點點頭,當作是回答。
「下次這樣可以先跟我講啦,就先不用來上班,啊妳手有擦藥嗎?」John 視線盯在我左手腕上。
「有稍微擦個藥啦。」我說
「下次手稍微包一下啦,不然會嚇到客人,不然就穿個小外套,之前還有客人看到妳手上這樣,問我妳是不是有憂鬱症,我都不知道怎麼跟他講。」John 說。
聽到這裡,我覺得心裡有什麼東西碎掉了。「等下我去找件外套來穿啦。」一如往常打用哈哈的方式帶過,我只想趕快找機會結束這個話題。
「那妳今天這樣還要上班?我幫妳跟李哥說就能回家了啦。」John 不死心地繼續講。
「能賺一天是一天啊,不然我現在回去也不知道要幹嘛。」說完,我聽到外面李哥在叫小姐們看台了,我起身走出包廂,不想回頭看見 John 的表情,我猜那個表情一定是憐憫。
就算跛腳還是能走路,一拐一拐的還是能走路。
浮木
經過走廊的途中,幹部對我說:「客人已經在裡面等了,啊這次也照舊喔。」點我檯的是位老客人,他的職業是建商,幹部們都叫他張先生,給錢很阿莎力,目的也很明確,來就是要做S,而且從來不殺價。進入包廂,看到他一如往常嘴角叼著燃燒的香煙,雲斯頓的煙瀰漫了他的臉,我坐到他身旁,從他的菸盒抽出一根菸,點燃後手指夾著菸在桌上無意識的輕輕敲打。
「今天心情不好喔?」他翹著腳問我。
「也沒有啦,就有點不舒服⋯⋯啊你今天還是一樣嗎?」
他瞇起眼睛看著我的手腕,「啊妳手這樣我也不好做什麼啦,跟男友吵架喔?手幹嘛用成這樣啊。」
「就吵架⋯⋯心情不好⋯⋯就這樣了啊。」我尷尬地低下頭,看著手上狼狽的痕跡。
張先生把手搭上我的肩,沒有不安分的動作,只是輕輕摟著我,「妳還年輕啦,那男生對妳不好就換下一個啊,外面帥的男生那麼多。妳現在來這邊就專心賺錢,錢賺夠了就走了,要把賺的錢存起來,等之後唸完書,想要幹嘛就幹嘛。」這是第一次張先生認真地跟我講話,如果只是一如既往虛情假意的陪笑,銀貨兩訖,我反而能自然迅速的轉換面貌進入狀況,但突如其來的關心反而讓我不知所措。
雖然張先生講的都是老生常談了,但他輕輕地摟著我的肩、輕拍我,這樣的肢體接觸讓我感覺到安心,我靠在他身上無聲地流淚,在上班需要假裝的情緒化表演,在這一刻得到一絲絲鬆懈,隨即又要擦乾眼淚,整頓好情緒,接待下一位客人。
行天宮的家,真的讓我病得更重了,這裡嚴格來說不算一個家,打開門就是一張雙人床,房間小的讓我的任何活動都被迫都只能在那張床上進行。在酒店還好多了,小姐休息室至少空間夠大,能讓我有足夠的空間吃飯、看書、跟小姐聊天,而且冬天還有暖氣呢。有時候我會覺得回到行天宮也沒有下班的感覺;上班也是躺著給人家幹,下班後見到阿昆大部分時間也是在被幹,為什麼我用「被幹」這個字眼來形容呢?有很多社會學者指出性工作者會用「角色距離技巧」來區分「工作時的自我」與「私領域的自我」,運用這樣的方式可以讓自己區辯性工作與性生活。
但與阿昆在一起的時候我還是如上班一樣疲累,一樣要表演情緒勞動,一樣覺得沒有被理解,找不到前後台的差異。我希望我們之間存在著愛情,可是我太清楚阿昆了,對他來說交往的目的只是為了有一個免費的性伴侶。存在於我們之間的只有無止盡的性愛,做完他就喝著冰鎮啤酒一邊看日劇,多數時候陪他看劇我總呆呆的盯著螢幕,但又不能完全放空,要對他看得無聊日劇表現感興趣,說到底都是急著跟人產生聯繫。
這種相處到底算什麼呢?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害怕每天下班自己一個人回到房間裡面。夜幕降臨的時候,房間寂靜到令人驚懾,那不是寒冷而生的寂靜,也不是光禿無遮的寂靜,是一種感覺正在緩慢地被稀釋淡化、沈浸到完全靜謐的黑暗中。
我真的病得很重,對那時的我來說,性工作的確留下嚴重的傷害;有時候甚至會想到我父親,六十幾歲的父親正是我客人的平均年紀。阿昆不在的時候我會帶不同的男生回來,清一色都是年紀跟我相仿或是比我小的,中年人會讓我有 PTSD,我用年紀來區分工作上的性與私人的性。
每天中午起床,餵貓、化妝、挑衣服、在麥當勞買午餐,上班,冬天時寒風灌入口鼻,會在酒店對面的超商買杯熱奶茶帶進去店裡,順便買酒精棉片跟抗菌紙巾,用來清潔下體。快到下班時間,如果沒客人的話就滑手機開交友軟體,希望誰來陪我度過難熬的夜晚,我的身體可以隨時盛開,不會有任何障礙。有些男人不一定會過夜,我深知這些人只是暫時地情緒移轉,像是煙火從天空爆開時的火樹銀花。依照過去經驗,美好的事物背後總包含著危險訊息:短暫、脆弱、不堅牢。當這些男人要離去時,我都故作鎮定,面無表情地說再見,其實之後在房間內大哭,哭到像是頭腦當機後就開始抽草,眼睛木然地盯著扭曲的天花板,身心已然分離,在心裡詛咒自己當場暴斃,不需要病因。
身心分離的秘密
有一次又跟阿昆大吵,他一連好幾天電話不接、訊息也不回,我擔心自己是不是要被拋下了,一早就叫車從行天宮坐往他深坑的老家。到了他家門口,來應門的是他父親:「請問妳找哪位?」「我要找阿昆,我是他女友⋯⋯」眼見他父親眉頭緊鎖,接著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好吧,他在睡覺,那妳先進來。」打開阿昆的房門,他正睡得香甜,這幾天的腦子裡面瘋狂的妄想、失眠,都在打開門看到他酣睡的神情轉為憤怒。
「你居然在睡覺,我以為你死了!你給我起來!」「妳幹嘛來?妳有跟我爸說妳是誰?」阿昆勃然大怒。「我說我是你女友啊,你家人根本不知道你交女友吧!」我已經氣到全身顫抖,提高音量繼續說:「還是你根本不想讓你家人知道你女友做酒店的?」「對啊。」阿昆想都沒想就這樣回答,彷彿一切皆理所當然,將近一年的認識,期間他巧妙地避開我想認識他的朋友與家人的相關話題,我一直不解他為什麼一直保持著微妙的距離,疑惑在今天獲得解答:性工作者這職業讓我成為無法端上檯面的女人,即便我不曾以我的職業為恥過。
後來我們這段關係還是毀了(幸好毀了),我沒有辦法在心裡繼續虐待自己。初識阿昆的時候就知道他有一個 Twitter 帳號專門放他的炮友與歷任女友的性愛影像,而我也在裡面,裡面各個女生有不一樣的 hashtag:黑肉、健身教練、小隻馬⋯⋯,各種對女性物化的字眼。下面網友的回覆更是噁心:「這女的好像被幹得很爽」「好好喔,羨慕」「奶子好晃」「推主真性福」諸如此類不堪入目的用語。
在跟他相識的這一年來,我感覺到與自己身份斷裂,好好相處的時候,阿昆是一個細心活潑的人,朋友眼中的開心果;另一方面我也知道他未經這些女生同意就把性愛影像 po 上網,多數女生甚至不知道在性愛過程中他有錄影。有時候嘗試說服自己,人都有「兩面性」,阿昆的另一面只是比較低劣而已,懦弱的我不想面對自己是知情的幫兇。我問自己:怎麼能知曉這些事又同時想抓住這個人不放呢?寂寞到瘋魔至此,確實難堪。
我也跟我保持距離,就像從身體分裂迸出另外一個人,那個人全然不知情,只是拚命跳著求愛舞的女子;另外一個人,她在制高點上不斷的譴責我:「妳是數位性別暴力的共犯,枉費妳讀的所有書。」我跟這樣的人交往,我能自稱為受害者嗎?我怎麼能跟其他阿昆拍攝的女生有共同體的幻覺?
多數時間我的精神負荷超載,面對這些性愛影像被散播的女生我抬不起頭來,一想到這種事情的新聞標題成為一組修辭,重申、簡化、煽動,內心湧現滿滿的無力感。遏止任何形式的傷害,就是停止跟他再有往來,誰知道命運愛開玩笑,我發現自己懷孕了。
我真的是請了一個鬼來打造我的房間呢,請鬼拿藥單大概就是這樣的感覺吧,我想。
雙子殺手
那天,半夜我叫了附近知名的牛雜湯來喝,天氣冷喝熱湯再合適不過,喝了幾口後覺得今天的牛肉味道很腥,於是我放下湯匙,起身走動。在房間走兩三步後,突然有反胃感,直衝到馬桶前乾嘔,「不會吧那麼衰小吧?」
冰冰買了驗孕棒給我,幾分鐘後浮出淡淡的兩條線,「欸,兩條線耶,明天晚上陪我去看婦產科,可以嗎?」轉頭問同為午場的同事冰冰,「沒問題,明天一起去。」接著我再嚥了一口牛雜湯,真的不行,整碗倒掉。
小時候聽媽媽說不要站在微波爐前面,微波爐的輻射會導致不孕,於是有一陣子我沒事就會站在微波爐前,祈禱自己是不孕症體質,永遠跟懷孕絕緣,但我還是懷孕了,可見這只是訛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