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關於展覽的實驗——《圖像與機制》兩次展
對於觀賞藝術展覽我們總是有種恐懼感,一方面慚愧自己看不懂作品,另一方面又懷疑是不是一切只是作者的「腦補」,其實作品根本沒有什麼東西。到底觀看作品有沒有一個相對客觀的標準,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難解的問題。偶然的機會下我參加了《圖像與機制》的兩次展覽,我們做了一個實驗,將展覽分成上下半場。上半場在南海藝廊展出,下半場則移師水谷藝術,第二次的展覽是第一次展覽作品的翻拍。這讓我有了一個機會思考前述的問題。

我想假裝我是一個旁觀者來看這兩次的展覽,所以我盡量直白的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而不涉及任何讓人頭大的東西。首先我會覺得從南海到水谷展場的變化太大。原本在南海藝廊當中,作品有一種比較舒緩的狀態,但是到了水谷藝術空間中會變得比較侷促,觀看的線索變得更加混雜而隱晦。我接著發現,這裡面部分的展品在水谷已經展出,可是另外有一些卻是用翻拍的方式,類似於展場的記錄,重新被貼了出來。對於這些複製品,第一個感覺是他們的畫質或是形式沒有那麼精緻了,我會懷疑再一次展出的理由是什麼?
這時候我注意到展覽的題目,「硬要展」這個概念讓我覺得這次展出更有一種諷刺的意味,好像他們有一種對抗的姿態。但是他們到底在對抗什麼呢?為了理解這件事,我會搜尋腦中各種具有反藝術特徵的展覽,然後我可能會找到關係,因此覺得興奮,也可能覺得這些作品不是那麼叛逆,或許原本他們就不是因應這樣叛逆的目的。當空間比較開闊的時候,作品比較可以有適合自己的呈現方式,也因此觀看的人反而有餘裕,從一個作品過渡到另一個作品,然後思考其中的關係。但是當它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我不得不將他們看成一組作品,可是在視覺上,它們又是那麼分歧。特別在水谷的呈現方式又更加任意——任意在此意指作品不像作品的擺放方式,譬如有些東西擺在地上,有些則貼在轉角。換言之它們不再是以一個單元跟一個單元的關係被觀看,而更像是鋸齒一樣參差呈現,這讓我覺得困惑,懷疑策展人是不是在亂搞?
為了進一步理解上述的疑問,我開始進入個別的作品,以搜尋「翻拍」與「原作」之間的關係。首先我看到吳孟真輸出為帆布的作品很醒目地位於展場入口。在沒有想起南海展覽的情況下,這會是一張看起來最為正常的作品,透過門口玻璃我甚至可以發現一巧妙的視覺關係。但是當我想起「重製」這件事,我會發現那個正常的觀看方式或許並不足夠,因為假設作者是有意識的操作,那她重新呈現一個「正常」的作品有什麼意義呢?於是我回想起在南海的展出時,它是實際掛在街邊的一個作品,當人經過的時候,平面的盆栽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好像它是真的東西,但是近看之下又是一個平面。同時在街道上的展出方式也有一種進駐乃至侵佔的姿態。但是這些特質來到水谷之後都消失了。掛在展牆上的海報,相對而言它不那麼像是一個實物,也不具有虛實的趣味性,它位在藝廊之中,與街道的侵占關係也不復存在,它純粹成為了一個展品,即使看起來仍然好看。

接下來我會看到汪正翔的火山照片,很刻意地貼在牆角。因為露出背面的關係,我發現這是一張明信片。一樣在沒有考慮南海展出的狀況時,我會覺得這是一個普通到不行的作品,充其量他就是有一個反藝術的姿態,將一個日常的物件,棄置在展場之中。但是如果我想起在南海展出的時候,這張照片可以約略被辨識出是一個螢幕的翻拍,我可能會開始思考,這跟明信片有什麼關係?因為這是我目前唯一能得到的兩個線索。一個直觀上的聯想是,明信片是一個告訴別人我在哪裡的東西,可是這張火山的照片,卻無法清楚地提供這樣的暗示。因此我不能說這張明信片是在火山拍攝的,因為我知道它是在螢幕面前翻拍,但是我也可以說,它旳確告訴我「他」在哪哩,就在螢幕的面前,一個平凡無奇的所在。

李佳祐的作品看起來與原來相差最少,他雖然將翻拍的照片掛在牆面上,然後把原作像是作為對照一樣擱在地上,可是整體而言畫質上還是很精細。純就這個形式而言,我會解讀這就是直白地暗示翻拍可以成為作品,而作品卻失去了原有的位置,只能在地下。但是當我想起這些照片在南海藝廊的環境中,觀者是可以約略的辨識出細節,於是我也想要在這次翻拍的照片中找到一樣的線索,然後我會發現他們幾乎消失了,即使這些照片的輸出品質看起來相當不錯。與孟真的作品一樣,我感到一種衰退。但是同時,如果我更細心觀察,我會發現這些照片是在展場整個翻拍的,因為他們有著畫框,跟一點點現場的光影。我會記起我站在南海展場時,我看得到那些隱微線索的時候,那個現場被記錄下來,但是視覺上卻已經無從觀察,我仍然可以啟動我的記憶去想像一個圖像,但是那跟之前由細微線索與心理的相互作用所得到的東西並不一樣。
.jpg)
在佳祐的對面我看到柯鈞耀的作品,投影的內容沒有改變,只是牆面上用描圖的方式將某些定格的畫面表現出來。比較在南海的經驗,這次我心裡有了預期。一方面是因為看過,所以我知道在人的眼睛看向鏡頭的時候,畫面會停下來。另一方面,那些在牆上的素描,也明顯預示之後會有某個人,就在那個位置看著我,如果我有發現這些素描都是面向鏡頭的人的話。這雙重的暗示與佳祐的作品形成了一種對照。一邊是重製之後的作品與原作無法疊合,因為細微的線索消失。一邊是重製之後,線索被刻意地放大。
孟真的另外一些作品佈置在展場的內側,我發現它們都是觀眾在南海展場對孟真作品的翻拍。但是相較於佳祐的形式,看起來更不像是作品,而像是純粹的記錄。我立刻感到一陣掙扎:我究竟應當仍然用作品的概念去理解,還是把他們當成一個事件的記錄?同時,當我這樣分類「作品」跟「事件」的時候,概念上到底意味著什麼?譬如前者應該更著重於視覺的表現,而後者則要看重行為的意義?假設我用前者的概念,我會覺得這些畫面完全平凡無奇,至多有一種強作藝術的味道。但是當我思考這些照片作為「行為」的意義,我就會發現這些照片是由許多人所拍攝的,他們像是孟真去擷取街景一樣,又擷取了孟真的照片,只是這次是由街道變為展場。有趣的部分是,雖然手法是一樣的,但是效果卻幾乎相反。在孟真第一次的操作中,擷取帶來了一種繪畫感,透過邊框與取景,這些尋常的街景被組織成一個自成天地的畫面。但是在參觀人的翻拍當中,這些自成天地的世界,又重新回到了現實世界之中,有著現場的雜亂。如果我再進一步觀察,我會發現每一位拍攝的技巧其實又不盡相同,有些人拍出來的照片,就像是場景的記錄,但是有些人卻同樣運用了構圖的技巧,讓孟真的作品與展場又產生了關係。

進入地下一樓,許戊德的作品與孟真有著相似的邏輯,他把參觀者拍他某一張作品的照片又展出來。然後在另一套作品中,將原本相框中的照片抽出,吊在半空中。我可以用理解孟真作品的方式去觀看他,但是我也可以將這一套視為一個整體,包括在南海展出的作品。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我發現在這兩組作品中原本獨一無二的性質消失了。而消失的原因是因為這些照片脫離了原本的脈絡。在 google 系列中,原本那一張照片應當是不准被拍攝的,但是當有人仍然去拍下他,那個規則被打破了。而在家庭相框當中,原本的規則就是那個相框,當照片存在於其中,被賦予了一種特殊的性質,一種真實的氣息與情感的羈絆,因為這是一個具有紀念意義的相框。可是當這些照片被抽出,真正引人注意的,不是那些吊在空中的照片,而是原來的相框,它裡面仍然有照片,但那像是相框所附贈的襯紙。一切的意義至此都幾近消失。google 出來的家庭場景,重新回到他們在網路世界樣態,一樣真空的存在,而相框還是相框。他人飽滿的家庭形象,只是凸顯了創作者在南海的一切努力是多麼地徒勞。

在戊德的對面,楊雅淳的作品維持了在南海藝廊展出時ㄇ字型的形式,但最大的那一張像是被撕爛而半垂掛在地上,而兩側的照片換成了這張撕爛照片在水谷現場的翻拍。我很輕易地可以辨識三種型態,一個是破壞後的原作,一個是原作在南海的翻拍,一個是翻拍在水谷的再一次翻拍。這三組照片形成了有方向的線條,由過去到未來。因此我可以聯想,如果這一組被撕爛的作品,在這次水谷的撤展中又被撕爛一次,那這樣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再進行一次?而如果可以,什麼時候會終止,譬如什麼時候照片會破爛到連作品的姿態都無法呈現,還是說它可以無限下去?在此處的問題,不是一個古老的現成物問題,而是現成物既然已經那麼普遍,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逼近那個極限?另外一個我看到的線索是,照片的紙張與顏色都變得很粗糙,不像南海展出的時候有一個均一的色調,跟精巧的相對關係。某程度上,我從南海那個特有的空間中被喚醒,我不斷地被提醒這些作品原來只是這樣。特別因為雅淳的拍攝對象本來就是不起眼的物件與線條,他們只要稍微偏離了一個正常的美學,好像就會形成崩壞。但是他們兀自存在於水谷之中,又像是某種宣言,彷彿說:我就是要以這樣的面貌出現。這讓我想起雅淳之前花卉的那一系列,那種堅韌的殘餘狀態,是雅淳作品最讓人動容的地方。
承翰與建寧的作品對我而言可以合在一起觀看,他們被放在一起,像是凸顯了他們各自借用了彼此的方法。建寧作品從靜態的照片變成了投影,而承翰從投影變成了靜態的照片。我感覺這是整個展場視覺上最好看的一個地方。因為它符合了一個展場的氛圍,細微的燈光,帶有抽象意味的圖像。但是如果我停留在這裡,我猜想我一定會被承翰嘲笑。因為他原來作品是完全不具有美感的特徵,當他把這個東西給表現出來,那不應該是一種精進,而是諷刺。諷刺的點在於,原來拆解攝影行為的作品,透過固定化的方式,變成一張照片,然後分解的行為又重新凝聚在一起。事實上我們應該把兩次的展覽合在一起。我們如果假想所有承翰作品全部在一個空間之中,那空間的兩端會是一個動態的自拍影像,跟不斷切換的照片,而在這兩組中間,又會有兩組,也就是多次合成的頭像跟街景。相對於原本的作品,它們更接近於一張我們習慣的圖像,也因此更讓我們感到寬慰,但是同時承翰站在外圍,觀看在其中的人。建寧的邏輯完全倒過來,如果承翰用合成的方式將時間取消,建寧就是用逐次顯現的投影把時間給召喚出來。他製造了一個與原作完全相反的意義。在南海藝廊時,如果風景可以被人造出來,我們就可以不斷重複凝視他們,好像無視時間的存在。可是當這些作品又放在一個旋生旋滅的狀態之中,那種永恆感又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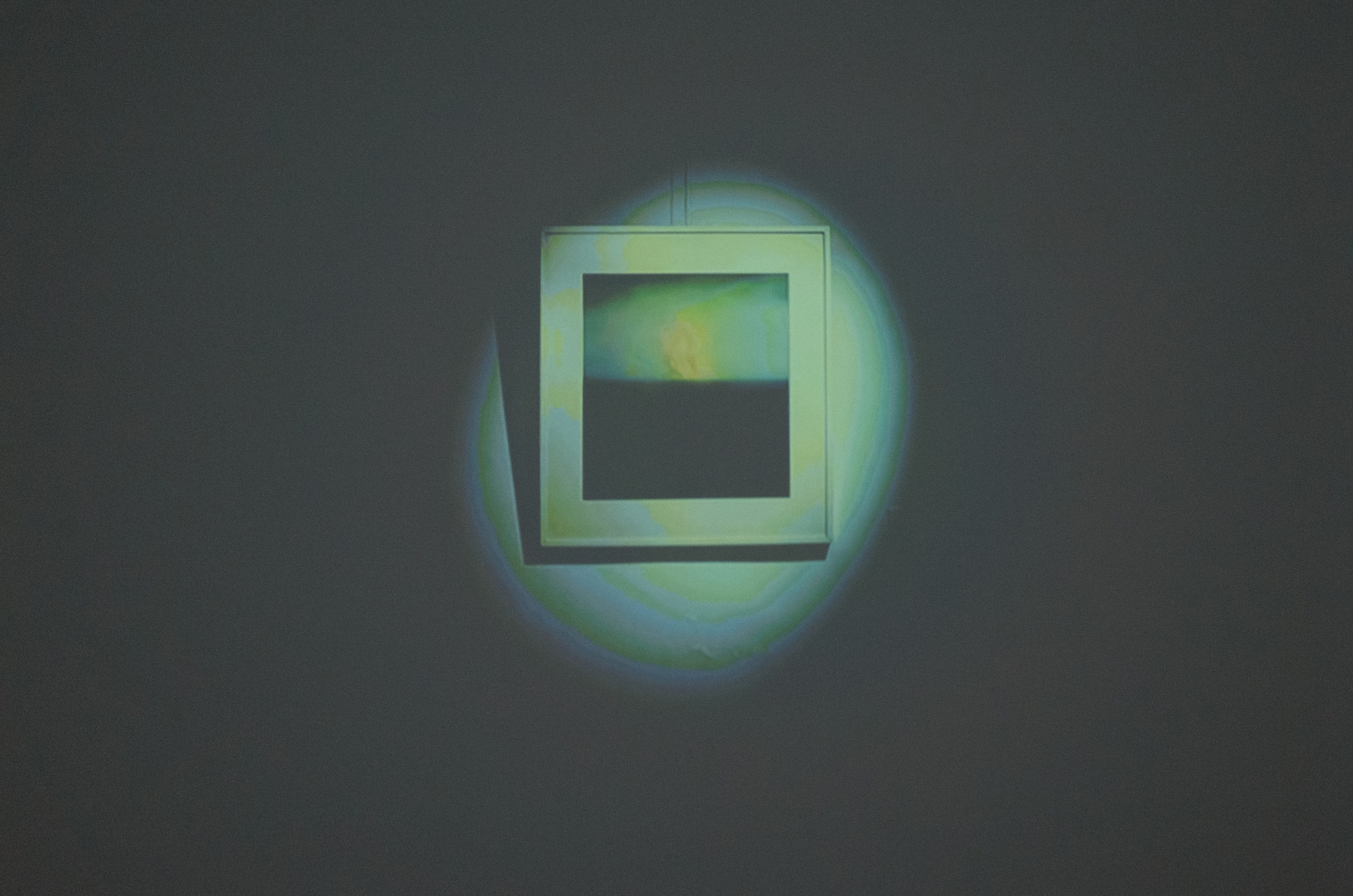
回到一開始觀展的問題,我發現在我觀察這些作品的過程中,我很難確立某一種固定的觀看方式,只能就個別作品尋找其內部的關係。事實上,我們幾乎無法提出一個涵蓋所有展覽的規則,因為每一個展覽都是孤立的。有時我們希望觀看者貼合自己的心境,有時我們又希望他們思考普遍的問題。但是有一點是共通的,觀看者可以試著描述作品,然後看其中發生了什麼。有時候,即使做完這個工作,仍會覺得一樣索然無味,但沒有這樣的步驟,我們就永遠無法正視藝術這件事。因為所有的創作都不可能完全為其它事物所替代,所謂的其它包括常情常理、社會意義、藝術脈絡、思想理論或是作者動機。創作的關鍵必然只存在於作品自身的關係,即使我也曾經期待一個展覽能在歷史上有他的意義,但這事實上並不能成為展覽目的,甚至連增添他一點點價值都無法。
表面上,這兩個展覽看起來都有一種自圓其說的意味。他的主題跟內容是等同的,譬如主題是圖像,所以拍圖像,主題是翻拍,所以一堆翻拍,主題是硬要展,所以硬要展給你看。某一些片刻,這讓人感覺是一種詭辯,但是另一角度來看,這顯示了兩次展覽的「分析性」。在康德哲學當中,曾經區分分析語句與綜合語句。分析語句譬如「所有白天鵝都不是黑的」,而綜合語句像是「所有天鵝都是白的」。我們可以簡單理解,前者是述語的概念已經在主詞之中,後者主詞與述語的關係只是經驗上的聯繫。而當我試圖描述這些展出的作品,我會發現這些創作者用一個獨特的方式與自己的作品產生新的關係與對話,而不仰賴任何作品以外的東西,某種程度上,就如同一個分析的語句。旁觀這個現象,讓我暫時從藝術的思辨中脫身,他們像是一個個騎單車的人,依靠自己推動自己,並且得到愉悅,而我一直覺得這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事情。我們當然仍能追問這種自給自足的樂趣有什麼意義,探詢單車要通向何方。但是我們也可以一起坐在上面,然後協力讓「我們」推動自己。
最後,如果要不能免俗地感謝這些願意配合我的藝術家,我會說感謝讓我體驗這種自我驅動的狀態,不管將來會通往哪裡,希望我們一起騎下去。
《硬要展——圖像與機制2.0》
展期:6月16日-7月3日 12:00-19:30
座談:7月2日 16:00
地點:水谷藝術空間(台北市萬大路322巷6號)
輸出:Metropoly Studios 指定/協力輸出
參展藝術家:柯鈞耀、吳孟真、廖建寧、李佳祐、楊雅淳、李承翰、許戊德、汪正翔
策展人:汪正翔
延伸閱讀:
消極作為一種「屏蔽」:關於《圖像與機制2.0》
【汪正翔】
攝影創作者。目前看得見,會按快門。
部落格:http://seanwang.4orma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