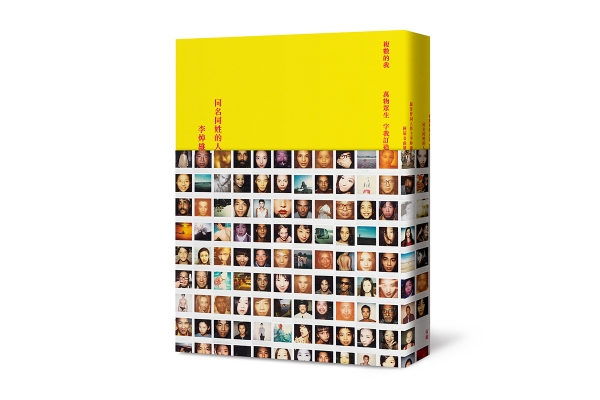
九月書摘|
同名同姓的人
我父
我是什麼時候才發現父親其實已不再年輕呢? 那天我坐在床上,在新分租的房子裡,時間其實已經不早,我起得晚,不再渾噩的時候正午都過了,但陽光居然還能穿過四周大廈的縫隙照了進來,微塵紛飛,新燙過的窗紗筆直透光,懊悔中竟有一種仍是日初,萬事更新的感覺,彷彿晨光還沒走遠,時間驀地生了寬容,也許我迎頭追趕追趕還來得及開始呢。於是,我便忽然有了努力的衝動,打算好好地利用這剩餘的下午。
然而電話突然響起,鈴聲急促,無先兆地劃破清靜。我拿起一聽,朋友第一句便說剛才想找我,但撥錯了號碼,電話打去了舊居,我父接電話時卻只說我不在,還仔細抄下他的姓名電話,說我回來後會告訴我,好像完全忘了我已經搬出去了似的。我後來回家,不經意向爸提起這事,他揚了揚頭,瞇起眼睛想了想,說:哦,我忘記了,又是當然又是歉意,語氣中竟還有一絲好玩。
父親近年好像沒以前那麼俐落了,好幾次好些簡單的話說到嘴邊也會搞錯,自己卻不自覺。有次我們去飲茶,他興致很好,像我們小時候一樣為我們張羅點心。他隔著兩桌茶客,叫停了推車賣粉果和叉燒包的,問明內容後,高聲說要「粉包」,還轉過來問我和妹妹要多少。賣點心的先是愕然,顯然也有點反應不及,接著便咧嘴笑了出來。我和妹妹都覺得窘,覺得爸爸好像無端被嘲笑,但竟然始終不知道,我們又不忍心說破。後來還是母親開口打發了對方。
然而爸有些事情倒是絕不含糊的。我新搬了地方之後,他堅持要親手為我做幾個書櫃,讓我二十多年來不斷亂買的書可以重見天日,不用再藏身於紙箱之內。他拿了鑰匙,斷斷續續地忙了幾個星期,效率不太高,成果卻一絲不苟:書櫃四個,用寸半厚的木板釘成,櫃邊還做了塑膠的軌道,可以裝上活動的玻璃門。撫著這木櫃,很像握著父親的手,一樣的大而溫厚,堅實而穩重─那是小時候爸爸抓著我的小手,帶我踏著大石階上幼稚園的殘餘的記憶。我以為我忘了,原來還一直記得:天高雲低,陽光朗朗地曬在印有我名字的小小的藍色塑膠書包上。爸爸走在前面穿著白色長袖襯衫,打著紅領帶,挺著腰,黑髮油亮閃滑,空氣中飛揚著一股爽利的髮乳的氣味,還有清早在路邊叫賣的蒸的白色腸粉的淡淡白米味道。記憶中的父親從來就是這樣年輕的,似乎也只能是這樣年輕的,就如我在他的心目中也永遠長不大。
以前住一起的時候,他習慣等我們都睡了,半夜會再起來查看我們有沒有鎖好大門。每夜乍醒總看見他坐在廳中,背著神檯燈垂著頭,黑色身影背後是一片紅光,像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全部都坐集一身。那神檯的紅燈,退縮在昏暗的一角,清早白天看不見,卻永遠守在那,暗中以血光呼喚黑暗,伺機而行。
搬來這裡之後,下了決心要清理雜物,一時清了幾箱東西,都用大紙箱裝著,準備全部弄完一併丟掉。那夜我很晚才回來,進門看到紙箱上貼著字條,彎腰一看,上面寫著:這箱有待明天拿去丟,因今天太累了。爸──簡單明瞭,不再逞強。我起來的時候失了重心,不意踏了空踩中了紙箱,啪的一聲,彷彿其中有點什麼頹然碎了。
|
|
有時我想,中國父子必定是最難互相諒解的。中國男子向來就羞於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心中想的都不好意思直說,成長是一次急促的情感退化。他未嘗不知道男孩最渴望的不是看來遙遠得不知用途的道德訓誨,而是直接單純的關懷,最好是放任得近乎溺愛的自由,然而長大後他便忘記了,又或是慣於抑制了,反過來嚴加管束自己的孩子。然後又過了許多年,他老了,孩童的奢望又復活了,倒又要從他兒子身上找回失落的關切的目光。但兒子呢,可還沒有到老得足夠還童的年紀,仍年輕得不屑兼顧這等婆媽微末之事。
小學作文課,但凡題目叫〈我的爸爸〉的,模範作文的模範父親總是那一類早出晚歸但回家後絕不會身心疲憊反而滿臉笑容耐心指導子女功課還能從不加以打罵兼且和睦鄰里加上言行得人稱羨的。我當時想:父親到底也不過是人呀,然而,為了投其所好,也就倒模仿製了一篇,後來好像還得到了老師在課堂表揚。這事每次想起來就更難過了,覺得親手出賣了父親和自己。
事實上,我印象中總覺得父親對我們過嚴,幼時的歡樂來自他偶爾的寬容。到了不再願意跟父母一起外出的年紀,那時候不怎麼喜歡他在家。我父親中年近視,所以不准我們看電視,他回家第一件事便是關電視機,於是一下子螢幕上的長劇的悲歡離合便即時灰飛煙滅。我那個時候和哥哥上下鋪睡在客廳,我睡下面。 爸上班前會坐在我的床邊穿襪子。小的時候我會抱他,但中學以後,我會裝睡,默默地不作聲地等他離去。他結婚前晚上去念英文專科學校,英文不成問題,唯獨在工作上有時要面對日本人,每次都不明所以,所以愈發感到外文的重要。中學二年級的時候他指定要我去中區的「青年會」學日文,要我每週混在那批三十過外的青年白領之中,呀依烏欸喔,好不尷尬。我一一賭氣陽奉陰違,表面奉行,暗裡反抗。那時我想我還年少,鬥他不過,心裡在等待,等我長大,而我終於長大了,結果中二便要戴眼鏡,讀大學的時候才驚覺日文對研究有莫大的用途,不得已重頭學起。
於是兩代的男人坐在反方向的子彈列車上,彼此重複著對方的路,注定要成為另一個自己,剎那相交,打個照面,想打招呼,但錯過了就錯過了。
我七八歲的時候趴在家中的床上玩槍戰,家裡沒有亮燈,我幻想自己是地球保衛隊唯一生還的隊員,正在獨戰隱形怪獸,目標是怪獸唯一現形的血眼:客廳中的神檯燈。久戰不下,怪獸老是不死,我一時情急,用盡了氣力把塑膠槍丟了過去。燈泡居然沒事,妖魔未除,槍卻從牆壁反彈回地板,碎了一地,壯烈犧牲了。我靠著微弱的紅色燈光小心地把殘骸逐片撿起。頭頂怪獸吊睛紅眼,一搖一擺地眨來眨去,在幸災樂禍。當時我心想,你可別狂傲,我始終是要報復的。
晚上我專心地等爸爸回家,趁他看來還不至於太不愉快的時候拿出盛著槍枝碎片的盒子,爸拿在手中一看,我預期他會罵,但更預期著屍體再生。他翻了翻便說:這都修不好了啊。我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爸對我說,乖,別哭,世上有些事,人根本就是無能無力的。我怎樣也不要相信。腦海中的卡通與超人向來都是死而復活的,怎麼早上還完整的好好的神奇死光槍,夜裡就毀了不能復原了呢。
然後是今天,我們一家再次上茶樓。爸坐在窗邊,低著頭要綁鞋帶,陽光正正地曬在我們的脖子上。雖然已經冬至了,但仍有一絲暖意。父親穿上了西裝結了領帶,笑吟吟的,也許是因為星期天,也許是我們兄妹齊集。在父親的意識裡,飲茶應該是占有儀式性的地位的,我大學畢業後第一天正式去上班,他要我早點起來,要請我上茶樓。我那天打了領帶,穿了襯衫西褲,扯著領帶跟爸說:好不習慣,這個。
爸說:慢慢就習慣了。
生而為我父,我想他總是不快樂的居多,人生付出的是這麼多,回報是那麼的少,而更重要的是年老已漸次自他的腦門把白髮一圈一圈地吃得微禿了。我突然記起老家的浴室,鏡櫃的門一拉開,裡面大半是風溼膏布與小罐的跌打藥酒。看得到的痠痛。他老了,但從沒聽過他問人存在為的是什麼這樣的問題。他不說不是他覺得不用說。只是他不知道跟誰說。
他是寂寞的。
《同名同姓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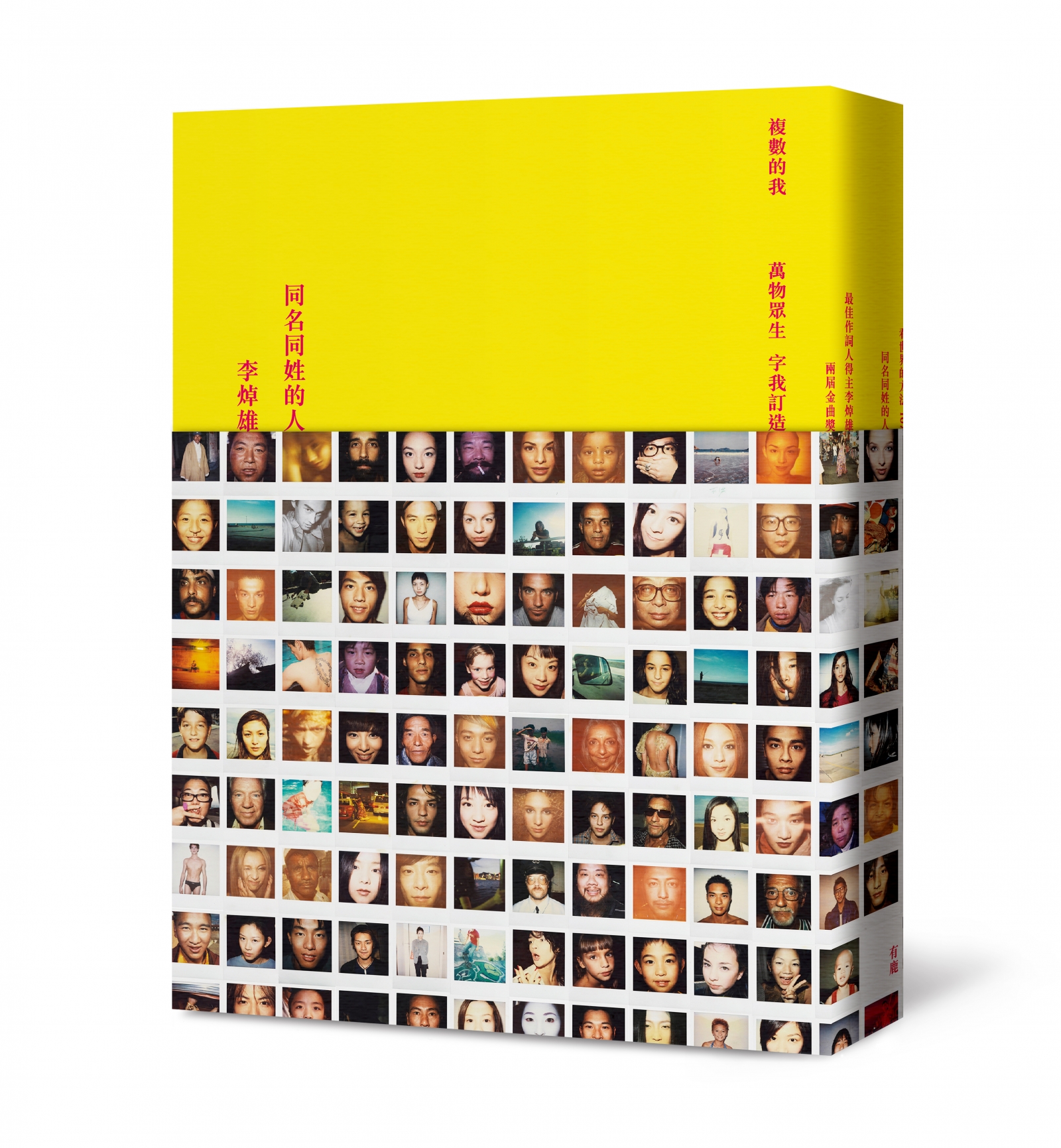
作者:李焯雄
出版社:有鹿文化
出版日期:2016. 09 .02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