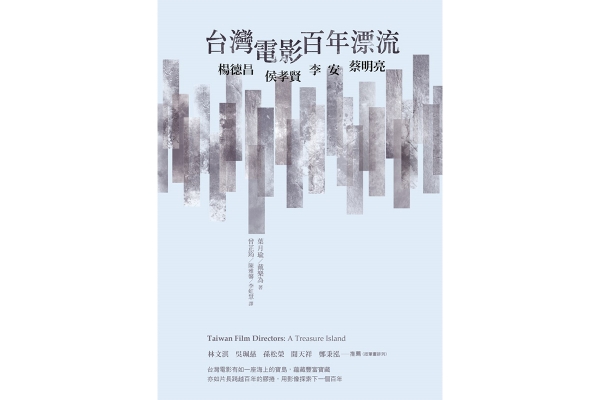
十月書摘|
台灣電影百年漂流
本土歷史,史詩敘事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以下簡稱《牯嶺街》)是一部複雜、悲傷的電影,也是在一段相當艱困的時間裡拍攝完成的。1991 年,已經處於谷底的本土電影市場繼續下滑。台灣製作的影片大多遭遇嚴峻打擊,在觀眾拋棄本土電影、轉向香港電影之際,台灣的電影年產量只剩一年四十七部(而香港在 1991 年有 168 部,其中有許多是和台灣的製片公司聯合製作)。侯孝賢《悲情城市》在兩年前獲得空前的成功,打破了台灣票房紀錄,也享譽國際影展,但對於楊德昌來說,這卻是一段伴隨著等待與不確定的時間,也是一段嚴苛的考驗。對於楊德昌的影迷而言,這段等待的時間相當漫長,自從《恐怖份子》廣受好評以來,他們足足等了五年。許多人懷疑新電影的下一步究竟是什麼?作為後解嚴時期解放運動的關鍵角色,《悲情城市》引起的動力是否能夠持續?而楊德昌能否交出一部像《悲情城市》這樣引起廣泛迴響的電影?楊德昌身為外省人,又是受西式教育的文化菁英,拍電影則大多靠自我訓練,他又要如何描繪台灣的黑暗歷史?總而言之,楊德昌的新作品並未使台灣影評人失望。就像《悲情城市》一樣,《牯嶺街》成功吸引了公眾的目光,也得到出色的評論,使人看見新電影在表達當代文化和歷史政治的重要性。
《牯嶺街》在台北上映了三個星期,獲得了總票房 940 萬左右的亮眼成績,也得到 1991 年東京國際影展評審團特別大獎。不過,影展單位想刻意隱瞞這部電影的國別(參見本章「金字塔的尖頂」一節),日本集團 Mico 由於背後有政府的資金支持,因此在楊德昌開拍之前,就先投資了此片的國際版權,使得《牯嶺街》當時是以日本電影的名義參展。同樣的手法也出現在侯孝賢兩年後參展的《戲夢人生》上。雖然表面上是國際品牌,但《牯嶺街》的實際主題則相當明確地指涉台灣本土的歷史,內容描寫發生於 1961 年,一個善感的少年謀殺者的故事。如同《悲情城市》,《牯嶺街》將一則本土、個人的故事提升為非常精細的時空結構。
楊德昌對於本土歷史的詮釋彷彿是在回應侯孝賢,為長期壓抑的思想解開枷鎖。《牯嶺街》和楊德昌其他作品最主要的差異在於歷史的特殊性,這部電影交織著許多不同的線索,由家庭歷史串起,穿插著不同的世代和階級。台灣與中國、日本、美國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纏繞,延伸出許多緊密的責任、同盟關係和相似性。概括而言,我們可以認同其中的中國元素為一種父權意識型態國家機器,這種中國認同試圖壓制代表恥辱的母性遺產,即日本殖民時期的殘餘。而美國則代表了青少年流行文化、高度的經濟成長和過度消費,它提供年輕人一個逃逸的出口,彷彿進入無盡的夏天。這四個國家象徵著歷史與文化,處處在片中暗藏線索,並延伸到電影裡的各種道具:日曆、雜誌、衣服、飾品、傢俱、錄音機、唱片唱機、歌曲、交通工具、武士刀、帽子、棒球棒、手槍、電影、甚至是電力能源。在這個中、日、台、美政治角力的局面下,以家族史的方式呈現,男孩和同夥之間因為受這些物品吸引,擁有共同喜好,在課後結盟為一個個小團體。台灣電影文化的活力便在這種對不同文化忠誠度的相互競爭中、在貓王音樂和本地類型乏味的例行公事的拉扯中,戲劇性地展現出來。
《台灣電影百年漂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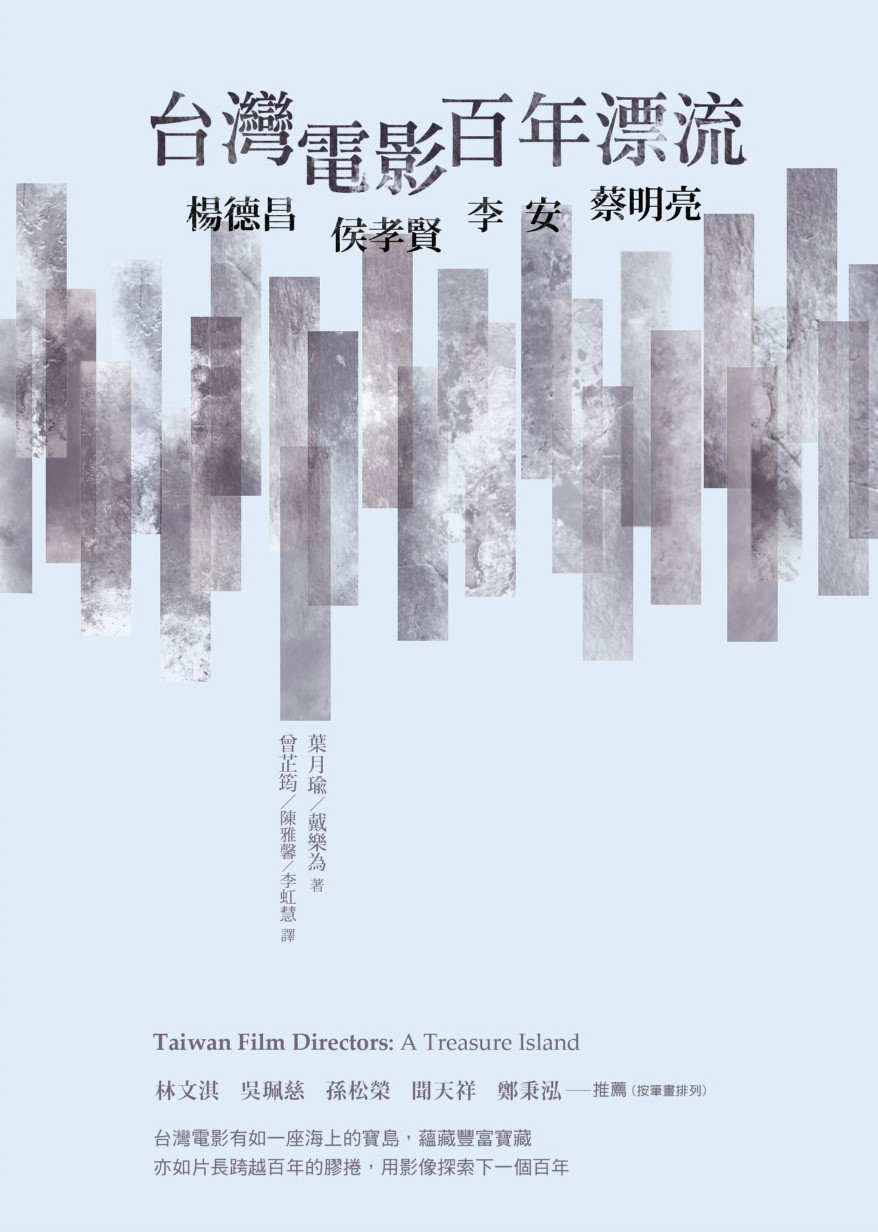
作者:葉月瑜、戴樂為
出版社: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 10.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