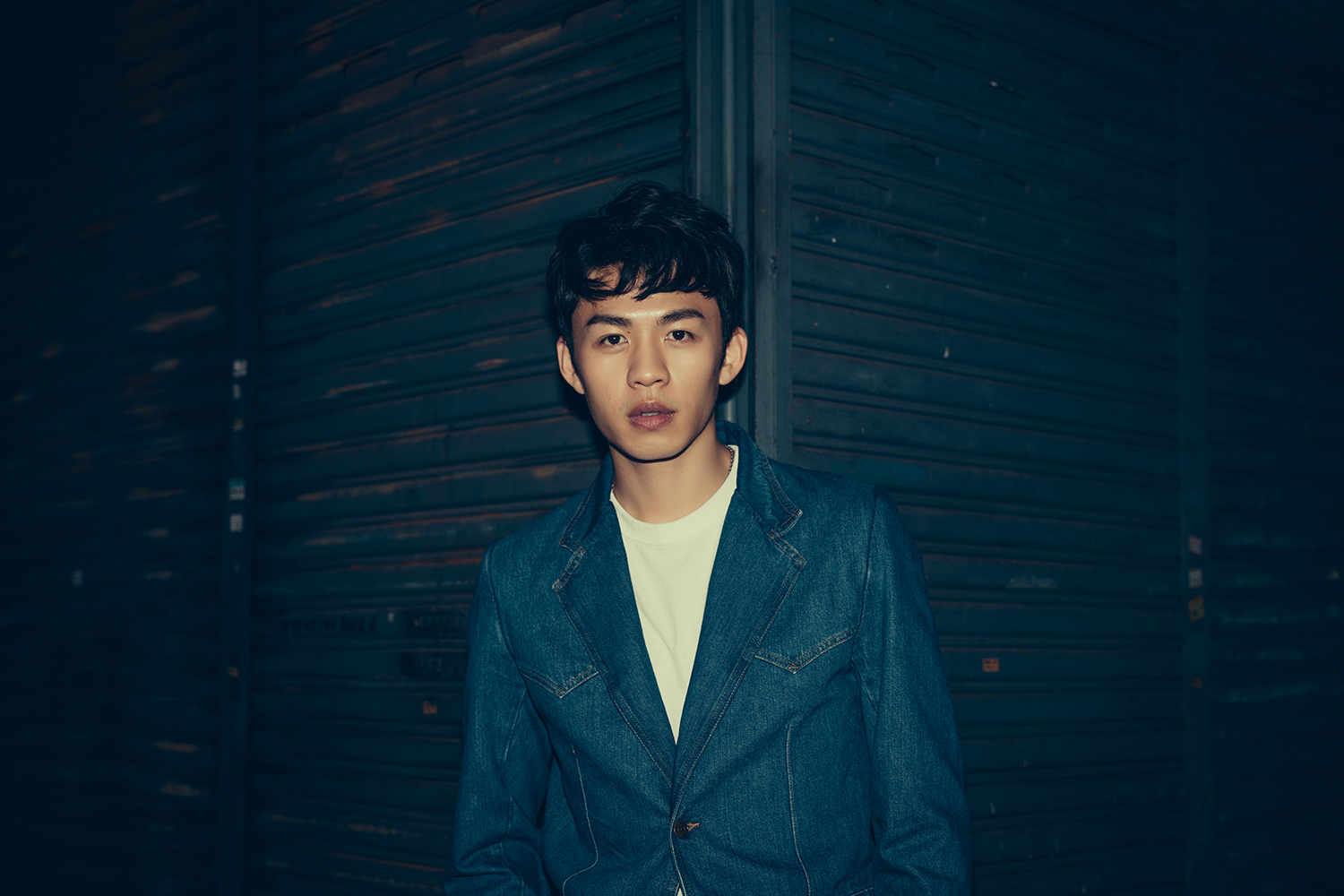專訪李鴻其:我是一個落地的演員
咖啡店二樓,李鴻其揹著側背包緩步上樓,坐定點了一壺名為沈澱的花草茶。2015 年,他以張作驥導演作品《醉・生夢死》出道,隨即拿下台北電影節最佳男主角與金馬獎最佳新演員兩個大獎,片中名為老鼠的年輕人一副小流氓樣,每日穿梭在菜市場和酗酒母親之間。
第一部電影馬上就有好成績,邀約當然不斷,只不過都是類似的東西,不是小混混,就是哭窮的,他說:「如果我演那些,現在就被定型了」。作為演員,他很有企圖心,在意角色的多樣性。於是他選擇沈澱,相隔一年,《幸福城市》才成了他的第二部長片,演一個有妻有小的正義警察,一個他還未挑戰過的角色。
我提起這部電影時有點議題先行,問他如何同理小張這個犯罪者/自殺者?他想了一下,語氣懇切,「嗯,雖然你說的那些在電影裡的確有講到,但對我來說,它還是比較偏向於我在演這個人當下的感覺吧。就是我可以拋開現實,我不是警察了,這個夜晚我遇到一個女孩子,她帶我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關於情節怎麼拼湊、怎麼說故事,那些問題是要交給導演的,對於李鴻其而言,與其討論議題與身份,他更關注角色的感受。
|
|
|
|
|
做演員,是精神活
年輕員警小張正氣凜然,不願擠進社會裡藏污納垢的隙縫取暖,於是幾乎是硬生生被結構暴力推了出來,大多數時候他壓抑自己,不輕易放聲哭泣。為了準備《幸福城市》,李鴻其像把自己出借給小張,他天天喝酒以讓載體更相容合適,持續一年沒有間斷過。
「我是一個控制狂。因為你在演某些東西的時候,心理狀態要夠強壯,那個東西我還想不到方法,你只能靠一些合法的東西例如酒精(笑),讓身體達到一種放鬆的狀態,這沒辦法。」演戲是將自己擲入險境,為了成全角色,他說成癮便成癮,下了戲又說戒就戒,演員工作,意志力不堅者勿試。
小張在電影裡台詞不超過二十句,非語言的表演常常比說很多話來得吃苦,必須用一個眼神、一個動作讓觀眾讀懂,「你看我被石頭打的那場戲,我哭了七、八次,都要那麼激烈,休息吃飯的時候就要一直哭,因為不能斷那個情緒。你一定哭過,哭第二次、第三次一定沒有第一次那麼有力量,所以你必須要一直保護著那個壓力鍋,不能讓它爆掉。我那場戲,哭了四個小時,身體真的是受不了。」
|
|
|
|
演員於身於心都是一份高壓的工作,李鴻其又習慣全給。你不曾有過害怕嗎?我問他。他沒有太多遲疑:「每次,每一部戲都會很怕。」他會怕對手演員跟自己的頻率是否對上,會怕自己能不能做到那個角色,更會怕對自身狀態的無法掌握。那為什麼想要一直表演?「真實。我覺得無論如何,就算表演沒辦法那麼漂亮,但至少它很真實。」對這份當下的真實著迷,讓他即使害怕,也要以肉身獻祭電影。
只是,燃燒心靈到一定程度,人是會乾癟的,於是他一直以來都有跟心理諮商師對話的習慣,讓洩氣的再次膨脹起來:「必須一直要,那是一個療癒。就是類似像一種鐘,敲了在你身上震波,讓你頻率或細胞會比較⋯⋯脈輪修復?可能像個精油按摩那樣的概念。」他形容諮商的方式很溫柔。明明不滿三十歲,李鴻其講起話來常是得道高僧的口氣,「所以演員真的不是體力活,是精神活。我有說過啊,演不出來的時候,是要拼命往自己身上打的。」得不到想要的情緒,演員必須自我虐待,一拳拳打死快樂,活口不留。
我是一個落地的演員
除了定期修復、保守心靈,落地生活對李鴻其來說更是必要的一步。「演員是需要靠時間的,你準備一個月跟一年,出來的東西是不一樣的。我有認知到這一點,包括接受自己的一些不足,因為我很喜歡看電影,我是影迷,我覺得演員就像一個藝術品。」藝術品三個字一出,他又馬上受不了自己似地說:「唉,說得那麼高級。」李鴻其的自嘲,實為人們都以為藝術品要進故宮博物院,而他口中的藝術是一種生活基礎。
拿獎後沒拍戲那一年,他考上哲學研究所重返校園,也打鼓聽音樂、玩攝影、認真看電影。他說,自己生活很簡單的,八點起床吃早餐,十點腦子還沒醒就打打鼓,吃個中飯後看個書配咖啡,下午三點到六點之間感性最多,則會拿來看電影或運動。
|
|
|
|
「很多演員不落地,紅了之後沒辦法回到正常生活。但現在我還挺舒服的,我是一個職業演員,我可以坐公車捷運大家不認識我,要幹嘛就幹嘛。例如說你什麼週刊拍我,對我無傷大雅、也沒人要看啊。我就是演員,我必須要落地,跟人接觸。」不斷強調「我是職業演員」,李鴻其的演員身份認同,從自重開始。
「你看我現在坐在這裡旁邊的人也不會看我,我髮夾這樣他們也不理我(笑),是吧?」他趕了整天通告,為了節省造型時間此刻頭髮上滿是彩色小髮夾,「像我那時去美國跟李安導演見面,我問他為什麼都在紐約了,他說,他只能在紐約,他在紐約都搭地鐵,在台灣所有人都認識他,沒辦法生活了。一個創作者不可能不生活的,我不希望有一天變成這樣。」
日常專注生活,接到劇本後,他則花心思了解導演。「像我現在即將要演的戲,我每天都跟導演聊天,聊聊最近看到什麼啊、喜歡什麼音樂啊、看到哪幅畫很漂亮啊,隨便聊。那他可能會說『這好醜喔』,你就大概知道他的點在哪。因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你要看導演要的是什麼,是導演找你來演戲,不是你找導演來導你。」演戲時他習慣放開自己,把所有都給出去,試圖與導演往共識的方向邁進。
他想起之前看過塔可夫斯基的書《雕刻時光》,裡頭一句話別有深意:「最好的演員是付了錢就演。」他說,這句話很直白卻也很高明,他始終認為電影是導演的作品,不是演員的。一個專業的演員,應該擁有內化導演語感的能力,因此他拍片不分商業、藝術,只挑想挑戰的角色。
|
|
|
做演員的,要懂導演的語感
會有這種導演為大的想法,多少與他的出道作有關,在《醉・生夢死》前,他不過是個熱愛電影、對拍片感興趣的大學生,對於演戲是白紙一張,但張作驥導演卻一步步引導他吸入老鼠的靈魂。「張導是從你身上把缺點變優點,老鼠這個角色全部都是缺點,他很屁、很吵、很鬧、很沒禮貌,可是他卻可以讓你覺得是優點。他對於人的那種想像跟看法,是我覺得真的很厲害的地方。」整個劇組生活在一起,從日常裡就被張導生吞活剝,素人演員沒有技巧怎麼演?讓角色成為他的真實樣態,就不必擔心這個問題了。
張導啟蒙後,李鴻其陸續跟幾位華語電影導演合作,幾年累積下來的作品在今年一次上映。多倫多影展上他鏡頭豐富,一次有三片入選,除了導演何蔚庭的《幸福城市》外,還有畢贛《地球最後的夜晚》,以及侯孝賢監製、劉傑執導的《寶貝兒》。既然在拍好作品前必須先了解導演,他當然對這些導演的風格有些觀察:「張作驥導演十句台詞,我九句都 freestyle,但何導演,因為他是從美國學電影回來,比較按部就班一步步來。我只給你一塊畫布,你就只能在這裡畫,但你可以畫得很好,那個演就是要演準。」但劉傑導演就又是讓他能無邊無際的人,彼此之間的溝通永遠只有「多一點」或「少一點」。
畢贛幾年前以一部迷幻的《路邊野餐》讓觀眾進入他如詩的世界,在李鴻其的經驗裡他是鬼才,拍片像在開學術研討會:「拍《地球最後的夜晚》時我通常都是晚上六點到,先化妝,化妝化一化就,好,吃飯。開始聊戲,這一場戲、這一個鏡頭,你覺得怎樣?然後聊一聊八、九點,好,休息抽根菸。然後,好,OK,架燈,弄弄弄架了一小時,看調度,覺得這調度怎麼樣?好,才開始拍。」
作為一個演員,他盡力尋找導演的創作節奏:「你要懂畢贛的語言。他語感是不同的語感,演員要符合他的語感。」2015 年金馬獎,他們一個拿下最佳新演員,一個拿下最佳新導演,同樣身為華語電影一股年輕能量,兩人都對做出作品的獨特性很有企圖心,於是那反覆討論的過程比演出耗時,常常到放了宵夜以後才真正開拍。其實李鴻其在《地球最後的夜晚》裡出現不多,但畢贛形容他是足球員,一上場就要得分,看來這位足球員板凳雖然都坐熱了,該研討的還是沒少的。
|
|
藝術是在血液裡的
今天訪問安排在晚餐時間,馬不停蹄一整天的行程,李鴻其看起來還是滿亢奮,思考時常用手指敲打桌邊。他出生在新北金山,靠海,從小不喜歡追求大家的追求,高中自己要求去讀華岡藝校,大學也讀戲劇系,這種選擇家人不盡然諒解,但他也不退。
他對藝術追求的一往無前,開始得很早,萬事總有個起頭,他的起頭發生在國中美術課,「我記得我拍過一張照片,那張照片拍得非常好。光很漂亮、一棵樹、一個人很俗氣地站在那邊,可是我的構圖就是很好看,現在看也很工整,分得了九宮格。」李鴻其在桌上畫了一個四方框,那張照片好像也顯影在那裡,「老師就說,那張照片真的很好。但『好』不是說像布列松那樣抓到決定性的瞬間,而是那個東西是很工整、完整、清楚的表達。」
「老師的鼓勵,打開我對於美的一個新的看法。我覺得藝術是要多多彼此鼓勵的,不要摧殘別人的心靈藝術家。」談到每個人心中的美感小種子「心靈藝術家」時,他有點激動了起來:「不要亂批評別人的作品,因為當你做出一個自己很喜歡的作品時,你是掏心掏肺的。」
國中美術課是他藝術魂的天啟,但要接著一直走下去不容易。他把路上好的壞的都視為命定,可能也因為這樣走得比較心安:「所有東西都是老天安排的,我相信這個,它是我的一個信念。包括我現在所有演的電影,都是老天要我去學習的事情。我覺得這麼想會讓我自己比較平淡一點,所有東西的不公啊或是什麼,有時候你想多了想不了。」
他突然有點佛系地說,佛教術語裡有個詞叫「智慧障」,人若是坐擁太多知識,想把一切都看得清楚,反而會被所知給綑綁。在電影這條路上,他以一顆隨遇而安的心去解老天爺下達的任務。桌前那壺「沈澱」的花草茶飲盡,他也準備好在不求甚解的路上持續出發。
採訪後記:李鴻其與其娃娃們
真實如李鴻其,翻開他的 Instagram,裡面幾乎全是娃娃:一隻小紅龍跟著他環遊世界,最近還添了一個新成員大犀牛(真的很大)。新手父母喜歡曬娃,李鴻其更是曬得沒在羞恥,狂 po 猛 po 用力 po:自拍、床照、配旁白的,各式各樣都有。
身為世故的大人,以為關於小龍的事背後總有些什麼,但他居然給我忍不住天真地笑:「就⋯⋯龍啊,呵呵呵,最近還買了一隻犀牛。你不覺得很可愛嗎?」是很可愛啊,但為什麼啊?「這很正常啊,你看到可愛的東西就是會想要收藏想要抱著他睡覺。你看我手機裡全部都是他們的照片。」他興奮拿出手機相簿滑啊滑,又要跟我分享他的小龍寶貝跟大犀牛寶貝。
他說,為什麼長大了不能抱娃娃呢?他想保有小時候最真的東西,娃娃可愛,欠抱緊處理。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