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好意思,這是一篇知更的專訪
剛發第一張專輯的時候,每回上節目宣傳,總要被問到:你為什麼叫知更?
問句演變到後來,後來的現場表演裡,他乾脆先聲奪人地問台下的聽眾:有人知道知更的故事嗎?
故事每次都講,卻不一定每次都一樣——最早的版本,是他在電台裡聽到知更鳥為十字架上的耶穌唱歌的典故;後來更多被提及的意義,是知更鳥在清晨唱歌,告訴大家新的一天即將到來。
好在自我介紹的日子沒有持續太久。2019 年他以〈風箏/白雲〉拿下金音獎最佳民謠單曲獎,名字前的介紹詞從「金曲遺珠」變成「金音得主」;隔年他參與的樂團 hue 發片演出,社群上開始出現自稱「全民愛 hue 推廣大使」的歌迷。後來知更接連幫田馥甄寫了〈懸日〉和〈乘著無人光影的遠行〉,他的聲音跟著田馥甄一起在小巨蛋響起,台下的人大概是平常自己演出時的幾十倍。
田馥甄寫他「知更的空心吉他撥著一點一點就把我帶走,讓我遠行去了」。陳建騏則說,「知更的旋律有著他特別的風味。」如今多的是有別人替他介紹自己。
這樣很好,畢竟他真的不太會說話。
那是你與生俱來
2019 年 12 月 18 日,知更的第一場 Legacy 專場,他每唱完一首歌,開口 talking 前都要像強迫症一樣先說一句「不好意思」。整場表演講了不下五十次的不好意思,講到後來全場都笑了,他自己也笑出聲,接著又說,「不好意思。」同場的嘉賓曾稔文氣定神閒地問他:「你是不是要我救你?」
下了台,知更就被宣傳的同事唸了。
他緊張不只是因為不擅長說話,也是因為真的太想做好了。「第一次演出一定都希望給大家一個好印象,你總是會想要多講點什麼——但是當你其實沒有東西可以講,但是你又想要多講的時候,你就會擠不出內容,就會變這樣。」
「我從小就不是很會在別人面前展現自己。我不是那種天生要做這行的人。」

他以為自己準備夠久了。人生頭一回站在一群人面前唱歌,是 2014 年的「敢夢想 敢追尋 ─ 軒尼詩V.S.O.P X SONY MUSIC 2014網路選秀大賽」,那年他剛從香港休學回台灣,還不確定自己到底要做什麼。想著可以接案做遊戲設計一邊玩音樂,結果一年過去,半個案子都沒接到,反而先在街聲上看到比賽資訊,心一橫,下定決心報名。
新聞報導裡還留著知更當年的自我介紹,那時他用的還是本名劉庭佐:「這是第一次鼓起勇氣參加比賽,因為覺得現在『是時候踏出江湖了』。既然堅持了這麼久,再不證明自己一下的話,就太對不起自己了!」
那場比賽他自彈自唱王力宏的〈公轉自轉〉,台下坐著陳建騏王治平和艾怡良,然而初次登台的成果不算太理想:上了台他立刻靈肉分離成兩個意識,其中一個旁觀表演中的自己,緊張和興奮讓腎上腺素猛爆分泌,歌越唱越快,最後稍稍心虛地說聲謝謝下台。
即使演出稍稍暴走,但後見之明地看,知更這一步確實沒有對不起自己。只是那一次比賽過後,他沒有一腳踏進樂壇,而是回到日常裡繼續教吉他、寫寫歌,參加幾個不大不小的比賽,直到 2016 年參加第十屆「myfone 行動創作獎」,他的自創曲〈瘀〉拿了個佳作,也讓福茂唱片看見了他。
簽進主流的唱片公司,但他也知道自己當不了主流的那種唱片歌手。好在發了專輯,公司也沒有讓他走上那一條路——沒有發片記者會、沒有電視通告、沒有八卦新聞稿,公司讓他用一個獨立音樂人最舒服的方式累積聽眾:音樂。
「我真的不是一個很會講話,或是能靠講話來吸引人的人。所以我就是好好地演出,給想要來聽我演出的觀眾,一個好的狀態。」
我要的方向
不必練習當個會講話的表演者,但加入唱片公司,最需要習慣的反而是溝通這件事。
做音樂向來都是一個人的事。第一張專輯《劉庭佐》,他一手包辦所有的詞曲編創作,自己當起製作人,還順手攬下專輯插畫和設計的工作。許多做唱片的手藝都是在 YouTube 上學來的,他把自己關在翠湖春錄音室(aka 他當時的家),慢慢磨出一張專輯。
不必有別的聲音干擾,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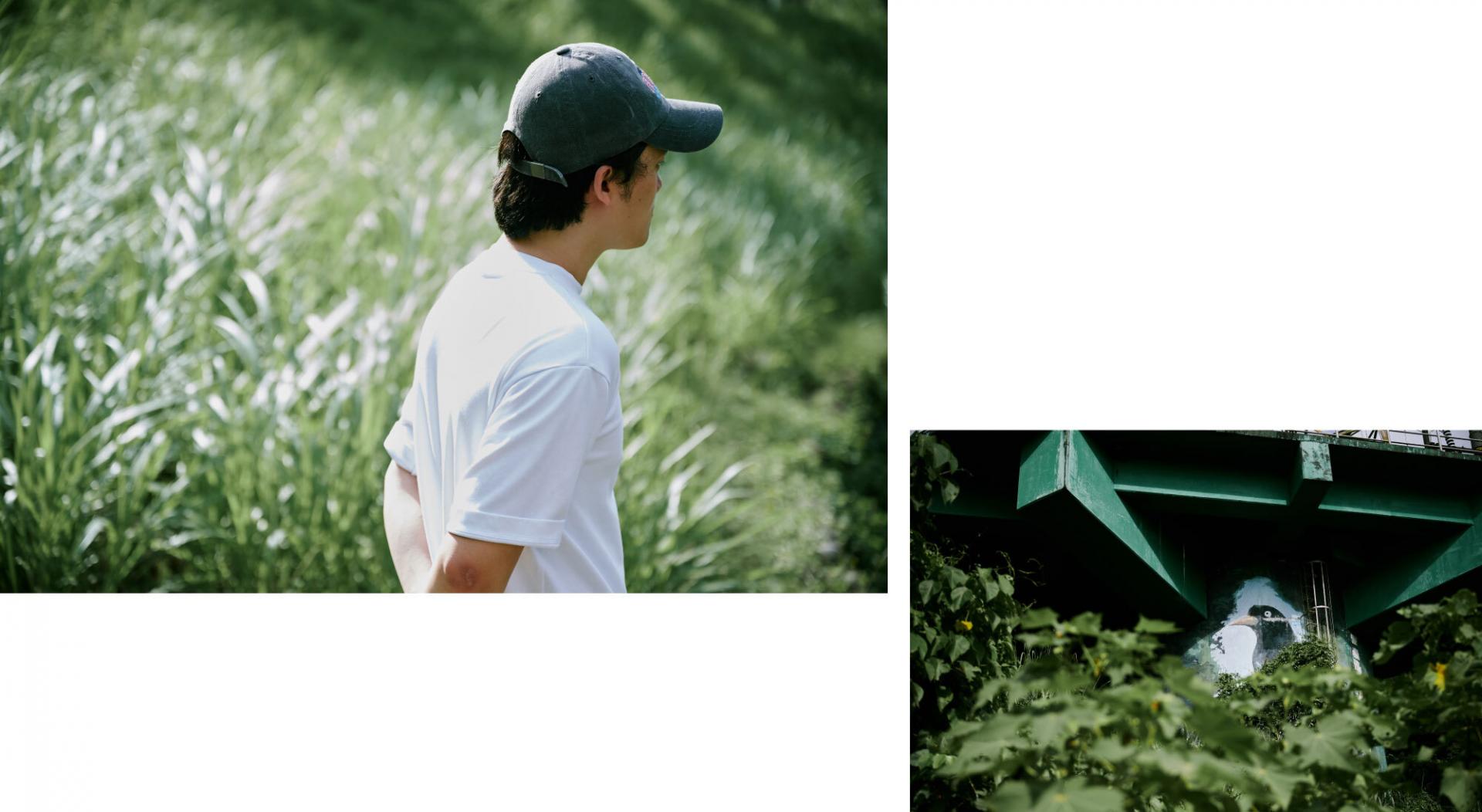

然而選擇加入唱片公司,看中的是製作資源能夠大幅升級。於是知更第一次走出翠湖春,進到公司正規的錄音室,面對眼前一群專業樂手時,他才突然意識到自己並不擅長溝通。
「那時是錄〈軌道〉那首歌,裡面有個弦樂的地方,老師拉得和我用 MIDI 作編曲的情緒不太一樣——當然老師人都很好,也都會以創作者的想法為主,但我還是會猶豫要不要跟老師說:你可不可以這樣做。」
回過頭來檢視,生活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必要的、不會影響到我的話,我不會去跟人家溝通。反正就是他就過他的、我過我的。」也不是覺得煩,而是知更的初始設定,就是很怕不好意思。「我是一個很不好意思跟人家溝通的人。」
他不是那種無法跟別人合作的人。知更的另一個身份是樂團 hue 的主唱兼吉他手,平時和團裡的夥伴一起做音樂,多的是意見的來回衝撞。然而對他來說,知更是只屬於自己的私密計劃,回到知更的音樂上,許多時候對溝通卻步,只是想對自己的作品有百分之百的真誠。
「我只是希望在做屬於自己的作品的時候,可以達到我想要的狀態。萬一沒有比我想像中的更好,那我會覺得只是在浪費時間,那是很痛苦的。」
這大概是能者多勞的某種典型——「大部份時候,因為我知道自己的音樂會是什麼樣子,再加上我是能在能力範圍內完成這些事情,那我就可以很順理成章地成為自己。當然如果跟其他人溝通合作,會把東西變得更好更有趣,那絕對是沒有問題的。但當你需要多一個心思去想那個『如果』,那就不太好玩了。」
為了保持想要的樣子,他學會精準。「如果我可以很精準地過濾掉很多不必要的因素,這個來回的溝通就會很快。再加上跟家人相處的經驗,會發現人不想變的時候,就是不想變,這其實沒什麼好強求的。所以我現在就是,有話再說,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有效率,快狠準。」
離恐懼只剩下一秒
倒是曾經有將近一年的時間,知更幾乎沒有出門,少有溝通,切斷了和別人的一切往來。因為恐慌症。
恐慌症第一次發作,是還住在上海的時候。當時他在電腦前玩遊戲,沒有預警、沒有原因,突如其來地就被恐懼突襲。「當下感覺真的要死掉了——雖然有在呼吸,但會一直覺得自己吸不到空氣,胸口好像快爆炸了。然後有一種沒有理由的,最深層的恐懼。那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有那樣的感覺,而你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到醫院檢查,醫生說身體一切無事,直到後來做了心理諮商和測驗,才知道這病在身體也在心理,名字叫恐慌症。
那段時間恐懼來得密集,「每次太陽要下山的時候,就會有排山倒海的孤獨跟恐懼。每天晚上都完全睡不著覺,處於一個已經精神疲乏的狀態,但你又要去面對恐慌症帶給你的情緒,整個就被榨乾了。」
但恐慌症最惱人的不是癱瘓了生活,而是即使知道病的名字和長相,每一次發作時,卻總不覺得那是恐慌症。
「每一次爆炸的時候,你都會懷疑是不是心臟有什麼問題、是不是真的要掛掉了。」生病是需要練習的,醫生說抵抗來自自我暗示,「你一定會還是會陷入恐懼的感覺,但是在比恐懼更內心深處的地方,你要知道這個絕對是沒事的。」
爆炸的痕跡烙印在他的身體上,知更開始回過頭搜索,生命裡曾經出現類似的陰影。想起小學的時候,台灣第一次出現禽流感,他在家裡咳了幾聲,立刻打電話給媽媽說,自己得病了、要死了。他以為沒有來由的恐懼和憂慮,其實早有線索。


到現在恐慌症依舊偶爾發作,但知道突然並非突然之後,心裡反而踏實。每一次被恐慌症突襲時,他會立刻躺在床上滑手機,或者打一通電話,假裝沒事,最後就會沒事。
或者可以寫歌——第一張專輯裡的〈祂〉,恐慌症巨大存在般顯影。
純粹是夜晚太刺眼/不是我不敢睜開眼/是誰的遊戲在眼前/我不敢假裝無所謂/「反正你別想離開」/祂要我知道——〈祂〉
對發病當下來說,音樂也許是最無用的。「當下我不覺得音樂的精神能量可以拯救我,那有點太浪漫了。」但他仍選擇寫:「但在這種狀態的時候,我會把我自己從感性拉回來,因為我知道我必須要理性,才能跨過這麼寫實的死亡的感受。」
音樂不是救世主,更像是一劑實在的鎮定劑。
你會用力地感受
把恐慌症寫成歌,是他難得用歌詞直球對決自己的心理狀態。但大多數時候,他其實找不太到方法,把心裡想說的話翻譯成別人也能看得懂的歌詞。
四年前知更帶著第一張專輯上馬世芳的廣播節目,聊到自己其中一個夢想是寫科幻小說,對方想了想說,「從歌詞來看,知更的文字是 OK 的。」
廣播節目看不見他的表情,只聽見知更小小聲說謝謝,聲音有點不踏實——畢竟前一秒他才說,「但我文筆很爛。」
剛剛被福茂簽下的時候,唱片公司要他放心做自己:一首歌長得近六分鐘沒關係、一張專輯一口氣塞 14 首歌也沒問題,一切照他原本的樣子。唯一的請求是:「你唱得那麼好聽,多唱一點嘛。」
多唱一點,也就是歌詞要多寫一點。但對知更來說,寫曲可以用感性腦,感受到什麼就寫什麼,行雲流水一氣呵成;但寫歌詞,他總要擔心視角不對、邏輯有漏洞,讓別人看不懂。需要切換成理性腦檢視時,他就當機。曾經寫詞痛苦到他一度在臉書粉專上發文哀嚎:「詞怎麼那麼難寫啊!」
他曾經做過「社交負面人格」的網路心理測驗,當中最突出的一項是偏執,總分 200 分裡,就佔去了 67 分。在音樂裡,偏執面大多就發生在寫詞的階段,「我覺得最有挑戰、最困難的東西,我就會很偏執地想要把它做到最好。」但偏執到底,他會察覺到自己努力過頭,「我知道接下來寫的東西是在強迫自己,已經不會讓我有興趣了,這時候我就會暫停。」
直到 2020 年,田馥甄的製作團隊找上他邀歌,demo 交出去之後由葛大為填上詞,成了那張專輯的第一首主打歌〈懸日〉。那是第一次有人給他的曲寫詞。看到最後的成品,知更內心震動:「看到不一樣的創作人寫出來的詞,很有趣的一點是——原來它的切入的角度還能是這樣子。」
他開始有意識地研究別人寫的詞。「以前我會覺得,每一句詞都要有涵義,讓這一句可以接到下一句。但是現在我看了其他人的作品,有時前面幾句是很順順地帶過,但是到最後一句的時候,會有一個很強烈的轉折點,然後整段話就會變得特別有意思。我覺得這種方式,好酷喔。」
他說的是林夕為陳奕迅寫的〈你的背包〉:
你的背包 背到現在還沒爛/卻成為我身體另一半/千金不換 它已熟悉我的汗/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環——陳奕迅〈你的背包〉
後來才發現,再理性的文字,最終能引發共鳴的,還是藏在歌詞反面的感性。就像當年他寫完〈風箏/白雲〉,給剛回到家的女友聽,對方聽到歌詞裡唱「他看著哪一天/要回家說再見」,眼淚就掉了下來。
一旁的她還原那個被歌詞擊中的瞬間:「因為我也是遊子,就會覺得對啊,怎麼回家了還要說再見呢?這句話就讓我不行了。」
才是最好
第一張專輯距今四年,他說自己真的沒那麼怕寫詞了。依然是挑戰,但不是真的害怕。不過話說回來,今年初知更才在臉書上宣佈正式從唱片公司畢業,回歸真正的獨立音樂人身份。「多唱一點」的限制器沒了,他說,「說不定哪一天我就不寫詞了。」
而他在台上說不好意思的次數,也確實變少了。
變少的原因之一,是他後來以 hue 的身份站上台,至少身邊還有兩個團員有義務分擔 talking 的重責大任(即使有人比他更不會說話)。另一方面他也放下了「一定得說些什麼」的心情,「我覺得只要是自己舒服的狀態,外在表現出來的氛圍,觀眾是會感受到的。你不必有一個接下來要幹嘛的心情,你要喝水還是講話,都是很自然、很下意識的。」


前不久文化部公告年度流行音樂補助名單,許多人在其中看見知更的名字,才想起他上一次發專輯,已經是四年前了。
出第一張專輯時,他用自己的名字劉庭佐當專輯名,那時他還在摸索自己的模樣。「其實我現在覺得第一張專輯根本就不應該叫《劉庭佐》 。因為後來我覺得『劉庭佐』的含義太大了,他其實不只是這簡單的 14 個作品就可以涵蓋,它只能說是『這兩個年的劉庭佐』。但那個階段的想法,大概就是那樣吧。」
名單上被暴雷的第二張專輯叫做《來時的模樣》。告別劉庭佐,迎接知更新的模樣。
曾經他在接受訪問時說,還沒做出可以代表這個名字的作品。到現在還不確定那個作品出來了沒,倒是知更這個名字,先有了第三種故事版本。
「現在知更對我來說,其實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他突然就開始說文解字,「『知』就是明白、領悟;『更』就是更迭、更新,所以就是明白它是一個不斷在改變的狀態。我覺得任何人事物本來就是不停在變化,知更的音樂對我來說,也是這樣的含義。」
2020 年,他寫給萬芳〈模樣〉。那是他第一次把自己寫的詞,連同曲一起交到別人手上。
聽人說/離不開的結局才是最好/聽不完的故事才是最好/看不厭的風景才是最好/留不住的那些才是最好——萬芳〈模樣〉
知更說,下一個樣子,才是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