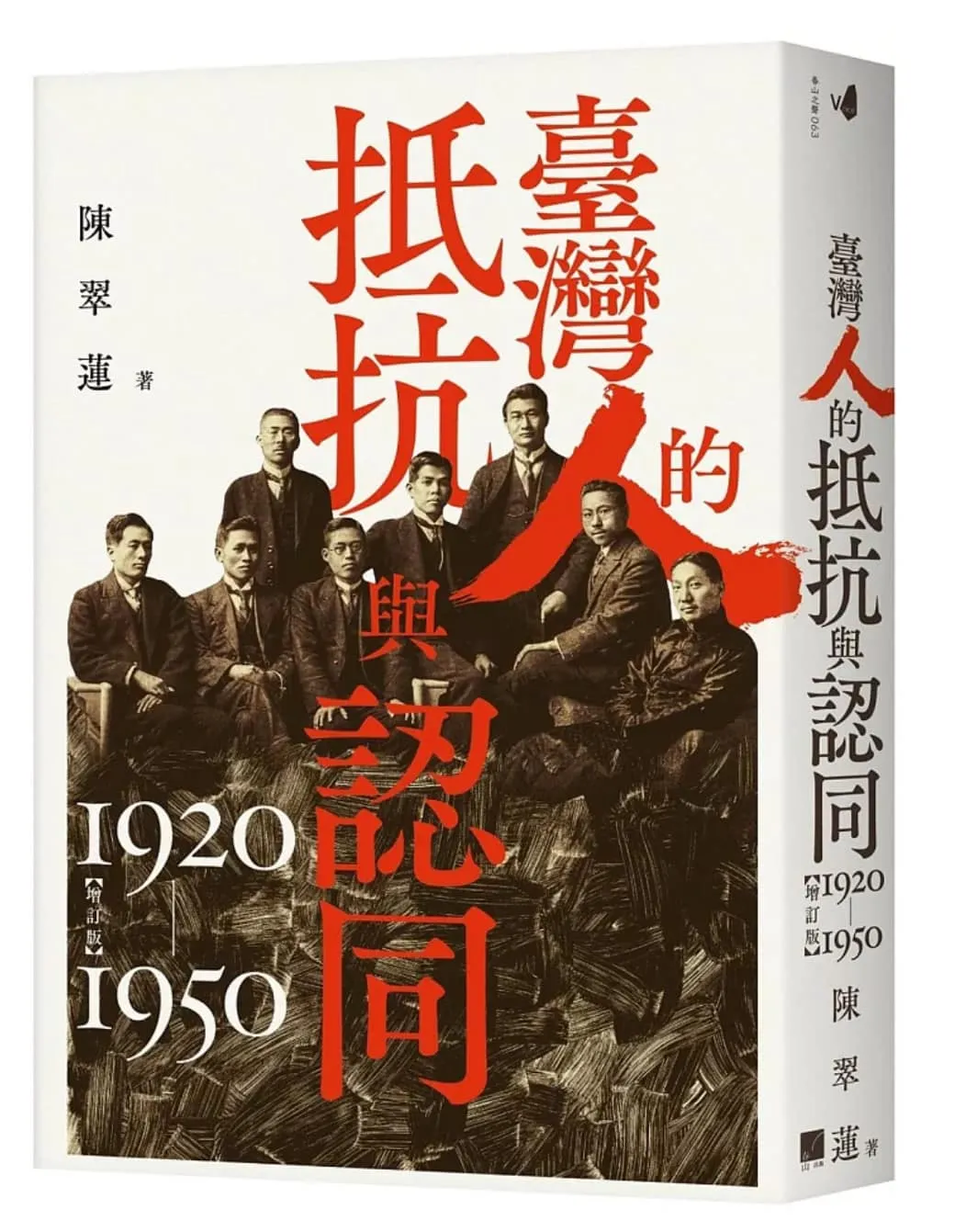「把壞份子抓起來」,但這不是一座這樣的島嶼──專訪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找答案
曾經,父親是想告訴她關於二二八的。
還在讀中山女中的時候,陳翠蓮就是同學裡最關心報紙頭版的那個。彼時是 1978 年底,中央民代增額選舉展開,黨外人士投入競選,與舊有的黨國勢力角力。陳翠蓮當時下課後習慣跑到臺大校門口,新生南路上的書店一邊立起黨外人士的「民主牆」,另一邊則是代表國民黨的「愛國牆」,雙方隔空交火,而陳翠蓮就只是站在那兒看。
就只是看。
當時的她沒有被牆上的民主口號打動。畢竟她是成長於黨國奶水的一代,小學時跟著蔣總統唱「姑息逆流激盪,世界風雲劇變,我們要沉著,我們要堅定」,寫作文不忘加上一句「希望明年雙十節可以在南京舉行」,把孫中山先生當作偶像,因為相信「良醫醫國」。
「因為我所受到的資訊就是跟著政府、譴責這些人。所以美麗島事件發生,我想說這些都是壞人,後來抓人的時候我也很開心,我還跟我爸講說,這些居心叵測的份子都應該抓起來,他們危害國家、顛覆政府。」
少數幾次,平日裡不談政治的父親被她激怒,「他就說你什麼都不懂,你就只是跟屁蟲,只會跟著統治者在那邊亂喊,你根本不知道二二八——」關鍵字一出,母親立刻衝出來和諧:「囡仔人出去會烏白講,會出代誌。」
她還沒來得及問什麼是二二八,就先遇上另一個二二八。1980 年 2 月 29 日,陳翠蓮一早起床看到報紙全版報導林義雄家中發生兇殺案,報紙上畫著林宅全地圖,鉅細靡遺地標示家中三人遇害的地點。「那時候覺得非常震驚,好像被電到一樣,頭皮發麻。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怎麼可能發生這樣的事?」
「怎麼可能」的意思是,她知道那有多不合理。「我們在那個成長過程,你知道這個政府對情勢局面的控制其實都很嚴密,怎麼有可能會有人能夠潛入林義雄家去,把一家老小殺了,而且後來還破不了案?這個只要是正常合理的人,你一定知道這個是誰做的。」
「以前你不用瞭解,政府都告訴你一套。但當你開始想要去瞭解的時候,開始去探索,你知道越多,你就不再相信那一套說法。」
進了臺大政治系後,陳翠蓮沒有忘記二二八,那是她急欲驗證的歷史真相。只是翻遍臺大研究生圖書館,戰後的老雜誌一直到 1947 年 2 月就消失了,下一刊再出現,已是 1947 年 5 月。
直到大四那年,臺大的同學裡開始流傳吳濁流的禁書,《台灣連翹》和《無花果》,從日治時期一路寫到戰爭結束,陳翠蓮一路往下讀,然後終於在吳濁流的敘述裡,遇見二二八。
「你看,從高三一直到大學畢業,我終於知道什麼是二二八事件。」
而陳翠蓮是那種人:有一個疑問,就要把答案找出來。
成為臺灣人
是在成為臺灣人之後,她才回過頭思考:臺灣人是什麼時候成為臺灣人的?2008 年,陳翠蓮寫下《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某種程度也是為了解答疑惑。
1920 年,蔡培火在《臺灣青年》上發表〈我島と我等〉,文章裡最沉甸甸的 8 個字,是他寫臺灣是「我等臺灣人之臺灣」——往後十年,這成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最響亮的口號。
然而那也不只是臺灣人的臺灣。許多人忽略了蔡培火的前一句,是服膺於統治者角度的「臺灣乃帝國之臺灣」。同一時代,自治運動的另一位健將林呈祿則稱臺灣人「支那民族的臺灣人」,蔣渭水更進一步提出,「臺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jpg)
1924 年 6 月 21 日,第五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代表抵達東京車站,二百餘名臺灣青年會員手持寫有「尊重民意、自由平等、民族自決」的小旗子,高唱「議會設置請願歌」歡迎代表們,並搭乘九部汽車遊行市區。
百年前的臺灣國族認同,終究和百年之後的「臺灣人」並不等同。但是到後來陳翠蓮才知道,有人對此是失望的。「我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去看,想要知道為什麼是那樣。我們是歷史研究者,我們並不是運動者,要去告訴大家一個民族主義的敘事,說我們從日治開始就主張臺獨——運動者才要這樣做。」
她舉例歷史學者黃昭堂在 1970 年的著作《台灣民主國の研究:台灣獨立運動史の一斷章》,原先黃昭堂研究臺灣民主國,用意在將臺獨精神上溯至 1895 年的臺灣民主國,「可是他去研究的時候發現——並不是這樣,所以他很誠實地寫出來,那時候臺灣人沒有想要獨立,我覺得這就是學術研究的態度,保持知識上的誠實。」
「如果我是要打造民族主義的話,我就會把他們解釋成,在日治時期他們就打算要獨立⋯⋯這個其實是國家常常在做的,國家的民族主義論述常常會這樣。但我們學科的訓練是,你要儘可能設身處地,知道他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他當時為什麼那樣想,每個人有他的時代限制。」
她甚至聽過有人因此貶低林獻堂、蔣渭水——不是非要把他們放到多崇高的位置,而是以今非古,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倒錯。
「我會聽到有一些人就說,不要紀念什麼林獻堂、蔣渭水,他們根本都沒有主張臺灣獨立,他們都喜歡中國,才害臺灣搞成這樣。這種看法是很非歷史的。」
「那個是非常政治意圖地去揀選歷史。但是你可以這樣揀選別人,別人也可以揀選另外一種,打造『臺灣人本來就想要回歸中國』的歷史。所以那樣的論述方式,其實對理解臺灣史沒有好處。人家也可以用跟你完全一樣的方式,去打造一個完全不同的論述。」
她相信的是歷史,而非主義。
悲情島嶼
1920 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才在萌芽的階段,與政治上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行的,是以文化作為抵抗殖民的戰場。在當時知識份子眼中的世界文明階序裡,臺灣處於「西洋-日本-臺灣」的底層位置,因此日治文化人採取的策略並非推崇本土文化以對抗殖民者,而是企圖直接引用西方文明,讓臺灣得以超越殖民母國。
當時文化菁英的眼光看出去,臺灣的一切都是落後的——思想是落後的。語言與文字是落後的,日治時期的小說家施文杞認為臺灣人的白話文常常出現許多口語贅字,或是日式語詞,容易「鬧出笑話」;張我軍更直接稱臺灣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就連臺灣土生土長的歌仔戲也被掃到文化的颱風尾,被貶低為敗壞社會風氣的「淫劇」。
在陳翠蓮看來,日治時期知識份子對本土文化的不自信甚至貶抑,固然是愛之深責之切,另一方面,也因為當時的臺灣人,早就不自信太久了。
「確實是在殖民地裡面,臺灣是比較特殊的。大多數的殖民地會以自己的文明、文化去對抗殖民者,但臺灣的情況是,我們是帝國的最邊陲,所以事實上它從來就不是文化中心,它也只是被統治,而不是自己可以形成一個強大核心的文化圈。所以我的感受是,我認為他們並不是看不起臺灣沒有文化,而是因為對臺灣有憐惜,而不斷自我提醒,我們要趕上進步的腳步。」
但另一方面,粗暴地援引外來的文明,卻也斷絕了文化往下紮根的可能。「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知識份子推動的文化運動,它跟底層大眾的距離就很遙遠。日治時期的文化運動提出很多種論述,但是這個東西可以推到多遠?其實向民眾推廣文化最好的工具就是戲劇,可是新劇運動基本上學的是西方的戲劇類型,不是從本地去取材,反而與一般大眾造成距離,這部份就自斷手腳。」

1925 年「臺灣文化協會講演團」合影於新竹,前排坐者:楊肇嘉(左三)、林獻堂(左四)、蔡惠如(左五)。 (圖片來源:開放博物館,典藏者: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日治時期文化人的心路軌跡,陳翠蓮也曾經走過。在長出臺灣人的認同之後,她也並不特別以臺灣文化為美——「其實我常常覺得臺灣好醜。那這個『臺灣好醜』,就是長期多重殖民的結果。但是『臺灣好醜』的話,那怎麼會有人認同?」
比起臺灣的美或醜,陳翠蓮認同的起點,是臺灣的悲情。讀碩士的時候,《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被尋獲出土,同時間陳翠蓮讀李喬的《寒夜三部曲》,小說裡日治時期的農民反抗運動與《警察沿革誌》史料相互對照,「我是發生歷史連帶感,看了覺得很感動,在宿舍裡面看到淚流不止,室友都覺得我是怎麼回事。」
「我當時很大的心靈的撞擊是,我覺得臺灣好可憐。我開始產生對這個土地的憐惜,我要想辦法幫它,讓它站起來。我不是因為感受到它的美才愛它,而是覺得好可憐好慘,我們臺灣人怎麼這樣被日本人蹂躪。」
悲情比光榮更凝聚,但或許已經是該走出悲情的時候。
「1990 年代之前可能是悲情,我們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是被打壓的,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辦法進入權力中心、做任何的決定。但是我覺得民主化之後,悲情的論述一直在消退——我們可以自己決定要變成怎麼樣的社會。」
因為有能力決定,所以更要時刻提醒自己:「我們有沒有用民主化後所擁有的權利,讓自己的社會變更好?」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過去威權的遺緒跟新的民主體制拉鋸,長時間的威權統治,其實改變很多人的思考方式跟對臺灣社會的認知,即使民主化了,可是有很多人還是戒嚴腦,尤其像我這個世代的人,他跟不上民主化的腳步,變成舊力量與新制度一直在拉扯,延宕了我們民主政治的進程。」
認同的關頭
她始終能夠理解兩股力量拉扯的那種撕裂感。很後來、在她不再唱「我們要沉著、我們要堅定」之後,陳翠蓮才知道,父親以前是會看《自由中國》雜誌的——只是在雷震案發生後,他立刻就把雜誌燒了。直到八〇年代,父親又開始閱讀黨外雜誌,甚至直接捐錢支援黨外人士。
那時的陳翠蓮甚至還沒成為臺灣人。還要過幾年,她才會脫下黏著已久的中國人認同。
「你看臺灣歷史就是很特殊,因為我們一直在換統治者,所以每個家庭他都歷經了兩種不同的統治,然後政治權力對一般老百姓的控制,在家裡很明顯地產生衝突,那其實是滿消耗的。」
但也因為如此,她知道認同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從前的她與現在的她,日治時期面對中國仍懷抱著祖國情懷的臺灣人,和二二八之後對於祖國破滅轉而尋求本土認同的臺灣人,都是會改變的。
「對很多人來講,認同問題其實不是只有情感,還有生存跟利益的考量。而戰後的祖國認同開始出現動搖,最重要就是這個:我的生存權被剝奪了。這事實上是跟日治時期的反殖民,我覺得是有連續性的,如果只從生存利益來看,戰前沒有辦法當日本人、戰後沒辦法當中國人,所以他要起來反殖民。」

1923 年 2 月,第三次請願委員與《臺灣民報》成員合影,左起:蔣渭水、蔡培火、蔡式穀、陳逢源、林呈祿、黃呈聰、蔡惠如、黃朝琴。
當如今許多人擔心中國文化強勢夾帶認同入侵臺灣,陳翠蓮倒沒那麼悲觀——因為在生存利益面前,中國的獨裁威權從來不會是一個好的選項。
「我覺得我還是滿有信心的。而且你會看到臺灣社會很有趣,長期以來都是這樣,一發生重要的事情,我們就會有一波青年運動。我們幾乎七〇、八〇、九〇年代都有,所以那個社會韌性其實還是夠的。除非這個社會的警覺也沒有了、我們政府也裝死,但現在看起來這兩個機制都還存在。」
是韌性,也可以說是幸運。
「臺灣社會有一個我沒有辦法明白敘述的集體穩定力量。我們的民情基本上還滿溫和的,或是你要說他仁慈也好,譬如說我們對殖民或威權統治者,我們都不會去追究清算,甚至我們還可以跟他們變成好朋友。但是臺灣社會也有一個基本的道德底線,我們希望臺灣變成怎樣的社會——像林宅血案發生後,臺灣社會集體意象就出現變化。民主化過程中,好多次局勢危險、眼看體制就要崩潰了,但沉默的大眾都能展現出穩定的集體選擇。關鍵的時刻,我們的集體意志就會出來。」
歷史告訴陳翠蓮,這是一座善於自我修復的島嶼,每一個歷史的節點都是必然。
過去如此,現在亦然。
《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增訂版】》
作者|陳翠蓮
出版|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