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野:「那時候大家都只想做我們自己的東西,但我們自己是甚麼?」
剛吹熄 60 歲生日的蠟燭!1954 年正式將農教公司與台灣電影事業公司合併,中央電影公司於焉成立。位於台北士林外雙溪,依山傍水,1961 年新建製片廠、錄音室、印片室等,1963 年中影總經理龔弘提出「健康寫實主義」的製片路線;1972 年梅長齡接任,開拍許多具有民族主義之抗戰影片,1982 年明驥總經理推動新的製片政策,大膽起用年輕企劃與導演,開啟了「台灣新電影」的紀元。隨著小野老師及所有前輩的腳步,那些蓽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日子,歷歷在目。

「那時候大家都只想做我們自己的東西,我們自己是甚麼,大家就開始尋找。」
我記得那一年是台灣很動亂的一年,人人都想出國、想移民。因為覺得台灣已經完了,第七艦隊開走了,美國宣布放棄台灣跟中共建交,非常多人花錢移民。那個年代的我,竟然拿到獎學金要出國,人人都羨慕我,可是我心裡面非常仇恨美國,所以我非常矛盾甚至還對外宣布我不去美國了。後來很多人都罵我說,這兩回事吧,去美國唸書的人多的是,你也可以回來啊。事實上,那時候的知識分子有兩種,一種是早就放棄台灣,努力考上台大,到美國去之後,就跟台灣 say goodbye。再見了,再也不受你們的氣,這是一種。另外一種是,美國有很多獎學金啊,一直期望台灣人去美國,受資本主義那一套,回來變成領導者,變成台灣好像殖民地的母國。我們從小成長的經驗,都是唱英文流行歌曲,所以比較有自覺性的東西,就是八十年代開始。
譬如李雙澤跳出來說,為什麼我們要唱美國歌,要喝可口可樂?我們能不能唱自己的歌?他唱美麗島,後來這個名字就來了。李雙澤很早就死了,變成一個標的。好了,校園民歌一開始,林懷民跳出來說,我們跳自己的舞。什麼叫我們自己?他裡面的我們「自己」是模糊的。可是他第一個標示,是跳我們自己的舞,哇那時候我們所有的知識份子(那時候大學難考,大學生應該算是知識份子)看林懷民崇拜得一塌糊塗,尤其他開始跳舞的時候,是不准有一點聲音的。有人照相,啪嗒一聲,他就說停,不對,我們跳舞大家不能拍照,安靜,再來一次。大家好崇拜。為什麼?喔!開始有點尊嚴了。文化開始有點尊嚴,就是說,我就是要這樣開始。好了,鄉土文學論戰開始。
那時候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失利後,始終很怕文學、電影,這些大眾傳播被左翼份子控制,所以他們非常嚴格地審查,小說、電影,更不用講電視,突然發現台灣人有作家開始寫鄉土文學,如黃春明、王禎和,甚至於後來的王拓等,他們突然有警覺,內部的組織裡面放出訊號。余光中有一篇〈狼來了〉工農兵文學,哇不得了啊!我們從小就蠻可憐的,看不到文化光譜的左邊,看不到自己內部的本土,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假的東西。左翼作家的作品,不能看,看了就抓起來,所以不知道中國的文學,從哪裡開始的,我們的起點是什麼,也不能推到清代,又不能推到日據時代。我們的起點,是國民黨來之後的文學才算。所以我覺得知識份子蠻可憐的,看不到左邊又看不到本土自己的東西,那我們還剩什麼?就是美國囉!或是很多人還是懷念日本,我們沒有自己的東西。
後來漸漸開始從舞蹈、民歌、蘭陵劇坊,也是實驗性的東西。話劇不是這樣很呆板的你一句我一句,是要先練肢體的。吳靜吉博士回灣來,就開始帶領大家做蘭陵劇坊,花了很長一段時間,練自己的肢體。現在回想起來,他是解放了被禁錮的肢體。那大家都不懂,為什麼一個舞劇這麼難,你一句我一句就好了,為什麼要先用肢體解放?我現在回頭看,他就是解放,從我們身體解放、思想解放,這後來也影響到我們 1980 年代之後,新電影浪潮找不到他要的演員的時候,就找蘭陵劇坊的演員,傳統的演員表演方式,他們不要,要比較自然的、肢體解放的。後來有新電影之後的導演,也學會拍電影前演員集訓,接受蘭陵劇坊的訓練,對演員來講也是個新的考驗。大家先熟悉,先做肢體。
台灣電影是在這個所有文化革命的最後一環,因為它需要資金需要投資老闆同意,然後需要市場完全消失,大家才願意反省,所以我覺得一切都是這麼巧。我們在 1980 年代還沒有什麼藍綠的概念,那時候大家都只想做我們自己的東西,我們自己是什麼,大家就開始尋找,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氣氛吧,那電影是非常非常偶然發生的。
.jpg)
到了 1980,像我這樣戰後嬰兒潮這一代差不多 30 歲上下,侯孝賢、楊德昌也許大一點過了 30,原來中央電影公司拍的是愛國片,正好也面臨一些瓶頸,投資了好幾部大的電影,像那時候《大湖英烈傳》、還有《皇天后土》,我必須承認比過去反共電影拍得好一點,而且品質也好。可是時代變了,變得實在太快,就是觀眾不吃這一套了,我覺得就是台灣另外一個被壓抑的生命力出來了。當時的總經理明驥先生,是個軍人出身,不懂電影。他其實非常有心想把事情做好,他找了吳念真,當時只是輔仁大學夜間部的學生,白天在台灣市立療養院做圖書館管理員,他覺得這個人非常有潛力,而他也不過是寫了三分之一的劇本(有一部叫《香火》囊括三個作家林清玄、吳念真加陳銘磻)。他就是看中這個人,覺得這個人好 ,然後好說歹說把他叫進來。
明驥用作戰、打仗的那個心態,說服年輕人說跟著我熱血,錢少沒關係,辦公室暗暗的也沒關係。陸續進來很多人後,辦公室設備很爛,看不到陽光,我們去跟他抱怨,他說中共當年是怎麼奪得政權的,在井岡山打游擊,在延安住窯洞才會成功,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子,就是苦一點,就是打仗,誰跟你開玩笑,還要享受,不然為什麼找你們這些年輕人,比較便宜啊!比較廉價啊!但是他真的會找,會說服你放棄原來的東西,他說服滾石老闆,我們叫他二毛,段鍾沂,是滾石的董事長。他竟然叫他不要做,唱片不要做,你進來上班啦,那薪水當然更不能比,剛好大家熱愛電影,為了熱愛電影,這個機會不錯啊!

大家形容中影,是一隻大恐龍在睡覺,這隻恐龍現在睡著了,我們只要進到牠的腦袋裡去,把牠喚醒以後,站起來是一隻巨大的恐龍。那我們這些年輕人很可憐,如果不進到裡面去的話怎麼辦,天天在外面一直繞,找老闆寫劇本,像我寫了五個劇本都沒人要,我從美國回到台灣來一整年都在寫劇本,都沒有拍成。當明驥來找我的時候,吳念真在那邊已經半年了,他告訴我不要進來,那時候我在報社上班。其實有報社要我去當主編,可是我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硬著答應明驥了。我覺得明驥之所以能夠那麼成功,是他跟你講話的方式,很能打動你。
等到 1982 年,機會來了,電視單元劇〈十一個女人〉,裡面有兩個導演很棒,柯一正跟楊德昌。李安也被我們看中,可是他還是學生。曾壯祥,他們同一屆得金穗獎,因為大家都不認識,都是用作品來評。後來選出張毅,張毅這個人辦過影響雜誌,他沒有過電影作品,老闆找過他來上班,做不到兩天就走人了,所以他不相信中影會做這個。可是機會難得嘛,好,四個人(編按:應該是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找來之後,我們就開個會,只有四百萬,一人一百萬,然後導演費七萬塊,就這樣子誤打誤撞的,這幾個導演就說一人分一段,重新寫故事,各自拍自己想拍的。每一個發行跟業務都笑掉大牙說,明驥怎麼找幾個小孩子來拍電影,是大學生的作品嘛,要是能賣我頭給你,我名字倒過來寫,講成這樣,我老闆也不敢講話。我覺得我們也沒什麼本領,東西拍了四段,真的是不商業,也接不太起來,各拍各的,只是勉強能夠看到時代在演進,然後用《光陰的故事》做名字,因為當時羅大佑〈光陰的故事〉還蠻有名的。那懷舊的心情突然起來,真的是拜市場改變,票房好到結束不了。
講好一個禮拜要下檔的時候,記得我還跑去跟明老總說,機會來了,賣得真的不錯,一個禮拜下檔,票房上不去。中影最厲害的地方,就是有十多家戲院,隨他調配,於是就讓《光陰的故事》放到西片的院線,打敗西片,大家興奮到難以想像,甚至有個假象是:我們的時代來了。然後開始趕快趕快,四個導演開始籌備拍下一部。然後另外一部,更讓我們有信心的是《小畢的故事》。侯孝賢找到一個題材說小畢的故事,然後他自己成立一家公司叫做萬年青,跑來跟中影談說一人出一半錢。那有好處,為什麼?只要一人一半,我們中影就很多規矩可以改變,攝影師就不用按照中影的,因為別人也是一半的老闆。《小畢的故事》也是用差不多四、五百萬拍的,賣了三、四千萬,我們幾個還被召見,年紀小小,還被新聞局長宋楚瑜召見,說國片起來了,賣三千萬,小兵立大功。我們那時候又開始籌備三段式電影,拍黃春明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送去的時候,當然有被注意,案子送上去的時候也是用騙的,騙到有點好笑。
後來就出事情了,尤其是《蘋果的滋味》。這部電影拍完了以後,文工會說有人寫黑函檢舉,要開一個公聽會,請大老們來看,這時候新聞局救了我們。新聞局長是宋楚瑜,發了幾個影評人來看,要參加國際影展。第二天所有新聞都一面倒。新聞局的政策,跟文工會的政策有點抵觸,因此救了我們。我打幾個電話給我認識的朋友,中國時報的陳雨航,黨外雜誌的吳祥輝。那時候聯合報有個記者叫做楊士琪,他就開始砲火集中地罵。就是這個火力好強,強到文工會一看糟了,這件事情不但沒有成功地把它禁掉,反而變成是一個宣傳。我記得第二天早上,我們在等飛機要到綠島的時候,打開聯合報,我們的照片出現在頭條新聞。我就告訴張毅,我們這一仗大概贏了,因為各報都支持我們,他一定會讓我們上片,後來一上片賣得非常好。
後來第二年我們老闆真的被換掉,我們老闆明驥是馬嘛,那來接他的姓林,叫策馬入林,時代一個翻轉三年半,這些新導演拍他們最好的作品,反而是在後來那個林登飛的時代拍的。侯孝賢拍了《童年往事》、《戀戀風塵》,楊德昌拍了《恐怖份子》,張毅拍了《我就這樣過了一生》、《我兒漢生》。時代的改變、觀眾的改變救了我們,給了我們在一個最不可能的地方,發生了那樣的事情。《光陰的故事》得了一些獎的時候,張毅上台講說,他不敢相信,像做夢一樣。這件事情比他想像中早了十年發生,他覺得台灣社會還沒有這樣的環境,會讓我們做這樣的事情,應該再等十年 1990 年代才等得到。1980 年代是一個戒嚴還沒有解除,每部電影都要被審查,思想檢查,怎麼會這樣就出來?
到底台灣新電影是結束在什麼點,大家的說法不一樣。有人認為就是在 1987 年,民國七十六年解嚴的時候,不是有台灣新電影宣言嗎?當時大家集合在一起,開始有很多反對聲音出來,媒體譏笑一些過度作者論的人。講簡單一點,就是指侯孝賢、楊德昌,過度作者論者害死了台灣電影票房。其實他們只拍兩三部,根本佔台灣很少的電影量,絕對不是他們害的,可是就開始包圍。因為很多保守派嘛!所以大家就發起宣言,一直說我們要堅持這個東西,政府應該鼓勵藝術電影,不應該拿錢去鼓勵商業電影。
很多外國人看,認為新電影就是結束在那篇宣言,因為宣言後就四分五裂。可是詹宏志先生就寫了一篇說,怎麼會呢?到 1989 年《悲情城市》還登上高峰,1992 年還有《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所以後來很多外國人看台灣新電影,也把 1990 算進去,甚至於也把李安算進去。事實上,它結束的原因,現在回想起來,的確是票房上成功地給了導演一些信心,可是這是錯的,觀眾不是那麼擁抱藝術電影。因為 1980 是一個消費時代,大量的娛樂產品出來,大量消費應該是更商業才對。加上很多人模仿新電影的模式,拍得四不像,片子一拍出來都不賣以後,片商的錢就轉向香港,香港比較商業。所以比較個人色彩的電影一不賣座,就被譏笑,像楊德昌《青梅竹馬》,賣得很差,侯孝賢《風櫃來的人》,賣得不好,媒體大量的譏笑,造成觀眾對國片的印象,都很難看,那鏡頭很長、很悶,造成媒體效應之後,片商跟著倒戈轉走了。
到 2001 跌到一年只有七部,2002 那個階段,政黨輪替,台灣社會進入到另外一種混亂。電影因為 WTO 談判,美國電影進來,雪上加霜,發行商控制在美商手裡,國片根本就被掐著脖子。新電影沒落後的十年黑暗期,那些沒有走的人真的很辛苦,十年熬不到一部電影拍,票房不到一百萬。可是新電影留下了一個典範是,後來的新導演都蠻崇拜這些導演的。時代越久遠,後期的年輕導演,他們欣賞藝術的角度變了,當年那些導演所拍的東西經得起時代的考驗。如果說 2008 年《海角七號》是台灣電影的復興,這些人全部跟過前面這些導演,當助導、當場記、甚至於當過道具,我幹過楊德昌的道具,我幹過誰的副導演,都很引以為榮。魏德聖最後還跑去楊德昌的墓園,他認同這個東西,這是我覺得台灣經驗中很難得的。對於台灣的身份認同,是從 1980 年開始,一路到現在,才是主流。文化的累積,至少有留下來。
如果從三十年來看的話,新電影留給台灣的電影文化資產,應該是很大的。但是它影響更大的是星馬地區、香港、華語地區的導演。他們崇拜侯孝賢跟楊德昌的程度,遠遠超過灣本地的觀眾跟導演。這個蠻奇怪的,很多新加坡、馬來西亞、或者是香港人都來台灣學習新電影經驗。我的記憶中,他們包括媒體對楊德昌過世幾週年的興趣遠遠超過台灣。這些文化雖然有在台灣發生,可是台灣後來因為政黨輪替,好像被藍綠的省籍惡鬥綁架了。所有文化發生的時候,都很快被這個比較綠、還是比較藍給淹沒,我覺得這點是我最失落的。金馬獎五十週年最佳影片頒給新加坡導演,那種感覺非常棒。電影影響到超出台灣以外的地方,我倒沒有覺得很遺憾,本來就是這樣子。當另外一批年輕人,很崇拜當年台灣新電影的時候,他們努力朝著這個方向,他贏了你,在國際影展得獎了,就證明說,我們這一代要怎麼再走出自己的路,失落或許有,但是就算了吧,因為我們至少夢想還實現過,有些人一輩子什麼都沒實現。抱怨歸抱怨,失落歸失落,還很慶幸,1980 年我選擇回台灣,大家相遇,或是互相不認識,發生了這件事情,還留下了些什麼。
【小野】
1951 生於台灣。1973 年開始文學創作。 1980 年代初擔任中影公司製片企劃部副理,為台灣新電影運動主要推手。1987 年離開中影,1990 年代初參與《尋找台灣生命力》電視紀錄片的策畫及總撰稿。至今完成逾百部之散文、小說、電影劇本著作,2013 年和柯一正導演等發起「不要核四 五六運動」,近兩年的時間內風雨無阻。為台灣重要之文化觀察者。
《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30(2DVD+1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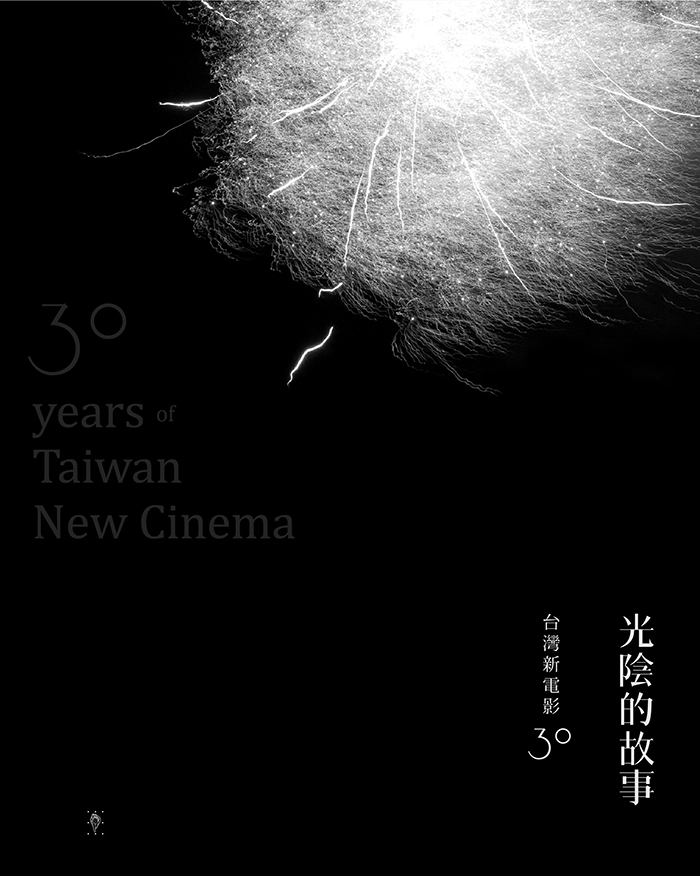
作者:謝慶鈴, 王耿瑜
出版社:行人
出版日期:2015. 07.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