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慶松:「我寧願要做的是很 soft 的台灣」
「就像羅丹是去石頭裡面找靈魂,剪接一如雕塑,我在做一個氣韻。」對廖桑而言,剪接是修煉,也是一個呈現。被稱為台灣新電影「褓母」、同時也是中影當時啟用的新導演之一,這些年同時擔任侯導的監製,並在多所大學任教,誨人不倦。位在萬芳山上的侯孝賢電影社,安靜的住宅區內,應如是生清淨心。

「我寧願要做的是很 soft 的台灣。」
我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開始技訓班,十二月進中影,侯導是六月大學畢業,七月進電影圈工作。民國六十三年,侯導幫中影拍紀錄片,叫《陸軍小型康樂》,我們就碰到了,一直合作到現在,到《聶隱娘》是四十一年。《陸軍小型康樂》這個片子應該數位修復,是 16 釐米的拷貝,是在龍潭陸軍總司令部拍攝,莒光日會放的,還有數來寶。那時候中影有一個短片部,是明驥兼的,陳坤厚當經理,都是用底片拍,因為也沒有其他紀錄的工具。我基本上都是在剪這種片子,金門、瑞芳等等,很無聊的紀錄片,但是很好玩,我們剪片,也沒有錄音帶,就把所有的聲音轉成光學聲帶,同步剪。然後每天站著,站到膝蓋好痛。這是我跟侯導合作的第一部片。
後來的總經理叫梅長齡,他本來是中製廠的廠長,做得很好,就被調過來。他們都是王昇系統的,包括明驥也是。梅長齡要拍《三民主義的世紀》紀錄片,找一票中製廠的紀錄片導演,一個人拍一個小時。我要把所有的畫面切開分出來,每個導演工作了起碼半年以上。梅長錕就是那時候的製作助理,每天睡在沙發上;錄音間的小弟就是杜篤之,他最誇張有四天沒有睡覺,站起來走路都是晃的。反正什麼事都是一團亂。所以在中央電影公司,最重要的不是劇情片,是為政治使命的紀錄片。我常常會價值觀混亂,現在當然沒有這種片子。民國六十三、六十四年完全在做紀錄片。我是躬逢其盛,然後就開始新浪潮了。
民國六十二年技訓班,後來一直辦到七、八期,才慢慢就沒有了。那時候有分攝影、錄音、剪接、劇照。屏賓、倪桑他們都是第四期。當明驥從製片廠、文化城、副總跳到總經理的時候,他用了兩個人,念真跟小野。這兩個人進去,剛好結合文學和政經社會的改變,他們有點像憤青、革命青年的味道,年齡跟我上下,也都是三十歲出頭而已。他們也把文學帶進了電影,像是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等,對舊世代的針砭。剛好台灣在七〇年代經濟社會都在改變,甚至於在解嚴之前,新電影先反應了,有點像股票市場,比較敏感。最重要的是,有一票留美的導演,經歷了七〇年代美國的變化,所以他們一回來,當然覺得台灣是老舊的,認為勢必要改,而且台灣那時候改革的氣氛很旺,所以等於新電影走在時代之前。對我來講,最大的刺激是,突然發現電影可以談感覺,談對社會的觀點,不再只是「三廳」式的電影。
在這之前,我合作比較多的是孝賢和坤厚,他們拍了很多城鄉差距、談環保的電影,像是《風兒踢踏踩》、《在那河畔青草青》,是和我們的生活很有關係的議題。後來《光陰的故事》,你可以看到這些導演的視野在改變。透過小野、念真的企劃,慢慢看到新電影的出現。你會去關心你身邊的事情、身邊的感情、事件,有一個觀點去看,也會把心底的很多想法傳達出來。電影不再只是純粹的娛樂而已。套一句大陸人講的話,開始比較「接地氣」了,開始是從泥土中長出來的花朵。以前不是,以前都是塑膠花,結果你進去聞都是假的,很刻板的感覺。這倒是我自己的體會。
新電影的導演很麻煩、很堅持。我一開始剪《英烈千秋》、《八百壯士》,有點辛苦,但是還挺簡單的。我的老剪接師父像是汪晉臣、王其洋(前幾年已經過世了),他們實際上都很會剪片子,像是《筧橋英烈傳》,都是很傳統的剪接。新導演跟他們已經沒有辦法合作了,因為他們講究的是感覺,電影不再是單純說一種戲劇性衝突的故事,開始思考內容、觀點、主題,相信所謂的文學社會性。可是對一個一輩子都在剪那種戲劇性觀念的剪接師,實際上是非常有壓力的。而且新導演又喜歡長拍,每個鏡頭都很長,剪接師總是回頭說:「欸,這很長耶,你要停嗎?」因為他們習慣性都是拍好分鏡的,譬如說這個鏡頭要用十秒,他頂多拍十五秒,都拍剛好給你。可是新導演就不是,人家導演拍是兩萬多呎,侯導他們拍已經三萬五到四萬呎,後來新導演就到五萬呎,到我自己當導演都十萬呎以上,越拍越長,剪接的困難度就越來越高。老剪接師們不能適應,新導演就不願跟他們合作,所以十年只有我一個剪接。我每天待在廠裡,所有人都看到我沒換衣服,公司拍四部片子,外面我還要剪四部片子,都是手工,我一年要剪八部到十部的片子,還要自己套片,套聲帶,套字幕,還要剪預告,套底片,忙到連睡覺的時間都快沒有。因為太累了,所以我有一度離開了,後來又回來了。
我覺得他們眼光真的跟人家不一樣,每個人有個性,看的都不一樣。楊德昌很喜歡從時事切入;萬導就從社會學的角度去切;曾壯祥就是純美學的;柯一正是無可無不可,什麼都可以;陶德臣很尖銳,我要什麼就是什麼,你不要囉嗦照做就好了;侯導就是「百變侯」,什麼都可以,什麼也都不可以,最後絕對是他要的。他最習慣說:「沒關係沒關係,我騙你我的頭就給你切下來當椅子坐。」所以最後我有一個倉庫都是他的頭,因為我每次都被他騙。這些人也影響我很多,我覺得本來我對電影是喜好,但沒想到被逼得要面對轉成社會議題、文學議題。我成長最重要的是這些人,他們觀點都跟別人不一樣,不再像傳統電影只看到衝突,他們有很複雜的想法,你要去解讀他們。有時候會需要溝通,會暗地裡心情不爽。但問題是他們一直在刺激我,覺得沒辦法應付,就努力看書,什麼都看,從美學一直看到佛學、神祕學,像是賽斯,我大概三、四十歲就看,我最喜歡的是《未知的實相》。
楊德昌是很慢半拍的人。他第一次用電腦剪接,本來講完話可以在神遊一兩分鐘,很慢嘛,剛好符合他的思考性格。結果那個按下去就好,人家說這是電腦,他就說:「嗯,讓我回去想一想。」躲了四天再來。他要回去想,這是楊德昌的反應。侯導的反應是另外一種。我們去剪廣告片,侯導看到電腦:「欸,好玩哪。」他就開始玩,玩到不亦樂乎。兩個人個性是不一樣的。楊德昌是念資訊管理的,去他家,白板上面寫的編劇,是電腦那種設計的流程圖:YES 到哪裡,NO 到哪裡,OR 或什麼。我看到嘆為觀止,有人劇本的 structure 是電腦程式的流程圖。我被逼得連電腦書都看,碰到這個人,你不看也不行。他實際上是非常細膩的,所以當你改他的鏡頭,他就崩潰了。我跟他剪《恐怖份子》,第二個鏡頭就分道揚鑣了。那個純粹是因為《恐怖份子》和《戀戀風塵》在一起剪,時間給我的壓力,我做了某些決定,他當然不爽,我也知道。兩個片子要一起趕金馬獎,我也沒轍,因為我只有一個人。那一年,《恐怖份子》得了金馬獎最佳影片。

我個人所見,從年輕到現在為止,我覺得這些人是最有負擔的,對他們自己的想法、社會的觀點、批評、美學、價值觀。他們一直想讓這個地方更好一點,想表達得更清楚一點。包括現在的念真,我永遠都覺得他背上有好多東西揹著。我們是戰後嬰兒潮,這一代是最慘的,成長也很貧窮,我們也銜接了後面的富裕,變成我們對下一代是放縱的,因為你不想讓下一代走自己辛苦的路。我被磨練過來,我很開心,對我這些新導演朋友們是很尊敬的。這一票人是我在世界上碰到的最堅持的人,他們拍電影可能不見得這麼商業,但是沒有這些人,台灣電影就沒有基礎,這是扎根扎得最深的時間。可能不符合娛樂的潮流,但我覺得這個年代對台灣電影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也讓我體會到所謂完整的人格,這些人的人格都非常高尚。他們的行為可能會有點浪漫,但是我覺得那種熱忱、堅持很難得。尤其是像「削蘋果事件」,那真的是萬導在辦公室把我們的垃圾桶快踢壞了。因為那時候政府以不能表達難民區的現象,拿出去會給人家笑的概念,叫我們要剪片子,我們把它拿下來翻底,把翻底交回去,原底保留,到時候再剪進去。有政策,我們就有對策。我覺得這些人都有自己堅持的理想,這是那個年代做電影最開心的部分。我覺得自己最快樂的是那十幾年。很累,累到有點每天都想罵人,但是走過來以後你會發現那十幾年,才是你最寶貴的時光。突然發現這個影片,可以跟你的生活、觀念完全融在一起,而且它會改變你,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覺得現在的電影就是缺乏一種理想、一種堅持,很可惜。現在只想票房,現在導演成長的過程,所受的訓練都是電視的比較多,所以看事情不再那麼尖銳,沒有剖析的。也許再一波的新電影可能會好一點,這些學院派的人所受的教育就是經典影片分析,他們是可以討論的,可能沒有像以前那些導演的渾然天成,從生長的環境過來,適應那個社會,他們有能力以外,還有一種融入與直覺,把自己所體會的表達出來。現在實際上真的「野生」的,就是趙德胤,只有那種類型才看得到,因為他沒有受過訓練,所以他有點像是新導演的那種態度,用的是生活的歷練去表達出來。可是問題如果你是學院派的,會變成引經據典一番,我覺得那都是隔一層的了。因為這一票導演成長的環境很優渥,跟生活底層接觸很少,甚至沒有到市場去買過菜,就不「接地氣」。
至於後來的《海角七號》,魏德聖聲勢浩大,去拍《賽德克巴萊》,背後有很清楚的設定,會讓你有壓力的。我寧願要做的是很 soft 的台灣。也許前面的人是建構了台灣的某些基礎,我希望後面的人,是把台灣最軟性的一部分,讓大家去感受,比方說台灣的母性、台灣人的性格。而且是非常柔和的,絕對不是那種壯士要出征了。你知道台灣人的悲情,要針對這個悲情去拍,就覺得壓力太大,我覺得何必這樣做?也許可以不要從歷史去談,而從台灣人的本身談起,台灣人跟這個環境的關係、台灣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台灣人的性格是什麼。我很想做的是這一部分,很軟性的台灣的性格,也是會碰撞到很多政治議題,但我覺得是最不會讓人家有抵抗力的方式。
拿大旗也不是說不好,但大家都很有壓力,正襟危坐。像是新電影導演他們就沒有這種壓力,他們就直接切入生活裡面,我覺得那個延伸的感覺應該用到現在台灣人的感覺,把他拍出來,像《稻草人》。因為終究那個年代,已經不在了,可是人是不會變的。生活改變了,但這些人,可能還是一樣的。我很想再去發掘台灣人跟泥土的關係。以前的導演是台灣正在改變,你們應該要怎麼樣,要去面對;現在轉型了,這個地方什麼讓你覺得可貴?讓你願意在這裡是什麼原因?我倒很希望去探討這個問題。也許不一樣的觀點,但是底層的感動可能是一樣的。
講台灣人很樸素的狀態,不是那麼嘻笑怒罵的,我覺得就很棒。《總舖師》對我來講已經有飽含很多台灣的元素,《海角七號》也有,只是用了一個太商業的情境,我覺得可以跟我們更接近一點,使用自己獨有的語言來表達,但一定得先符合這個時代的味道,因為時代已經進步到這個程度。天時、地利、人和要自己去掌握,要說自己的話。尤其我認為往後幾年,更需要我們說台灣的魅力。大陸現在充斥放縱到極致的商業語言,台灣要做自己的語言,做的很漂亮,讓他們覺得台灣人可以做出那麼漂亮的電影。
我教書剛好十幾年,成長的這一代,都一直跟我一起工作。有的出去了我還是當他們的顧問。而且我的學生,事實上都是台灣最好的,這幾年的金穗獎都是他們拿的。當然我也告訴我的學生,台灣人要競爭還是得往大陸跑,但一定要透過對大陸的了解,再決定拍什麼電影。大陸拍片都找台灣導演,他們要台灣年輕人,才能拍出所謂小清新,林育賢都還不像,《小時代》都是台灣北藝大的團隊。未來很清楚,我們要發揮台灣人的觀念,做兩岸可以接地氣的,是台灣性格的展現,南方人的溫柔,就會在影片上看的到。你可以旁觀整個大陸,有距離的來描述事情,剛好我們個性比較溫和,影片需要這種情感。我個人認為這幾年的畢業生,可以把電視劇的所有導演全部換過。現在看的人生劇展、學生劇展,許富翔拍的《十六個夏天》,我覺得年輕導演都有機會,我們沒有這個市場,但大陸有,台灣電影要做的好,要拍出屬於台灣的電影,要發掘台灣的美。
廖慶松
1951 年生於台北。是電影剪接師、導演、製片人。1973 年考取中影電影技術人員訓練班。1980 年代,一人身兼多部電影剪接,有「台灣新電影保姆」之稱。其中包括楊德昌的《海灘的一天》、《恐怖份子》與侯孝賢的《童年往事》、《戀戀風塵》、《悲情城市》,以及萬仁的《超級市民》等等。導演有《期待你長大》等等。2002 年獲得金馬獎最佳台灣電影工作者。2006 年獲頒第十屆國家文藝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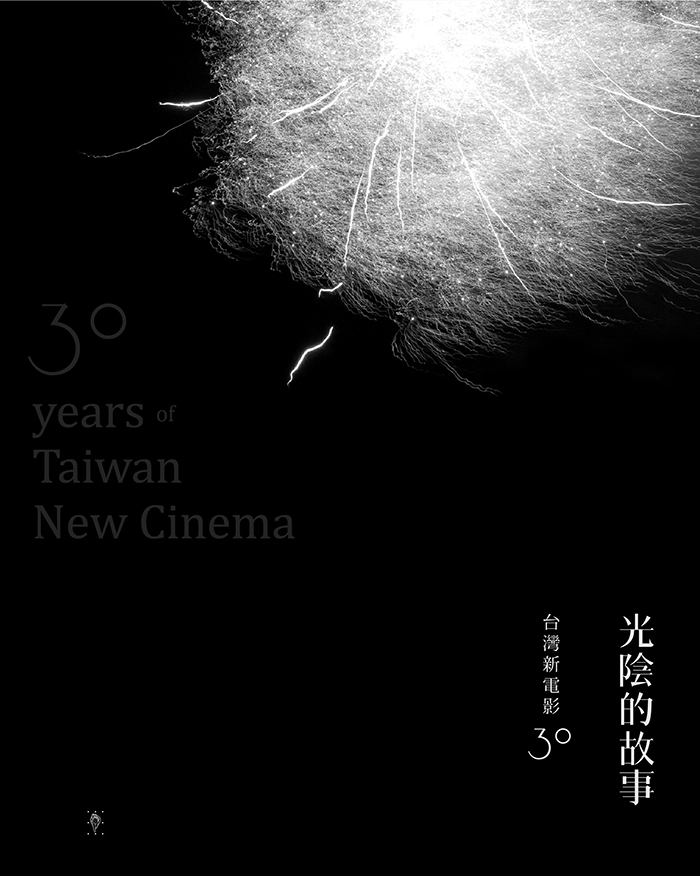
作者: 謝慶鈴, 王耿瑜
出版社:行人
出版日期:2015. 07.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