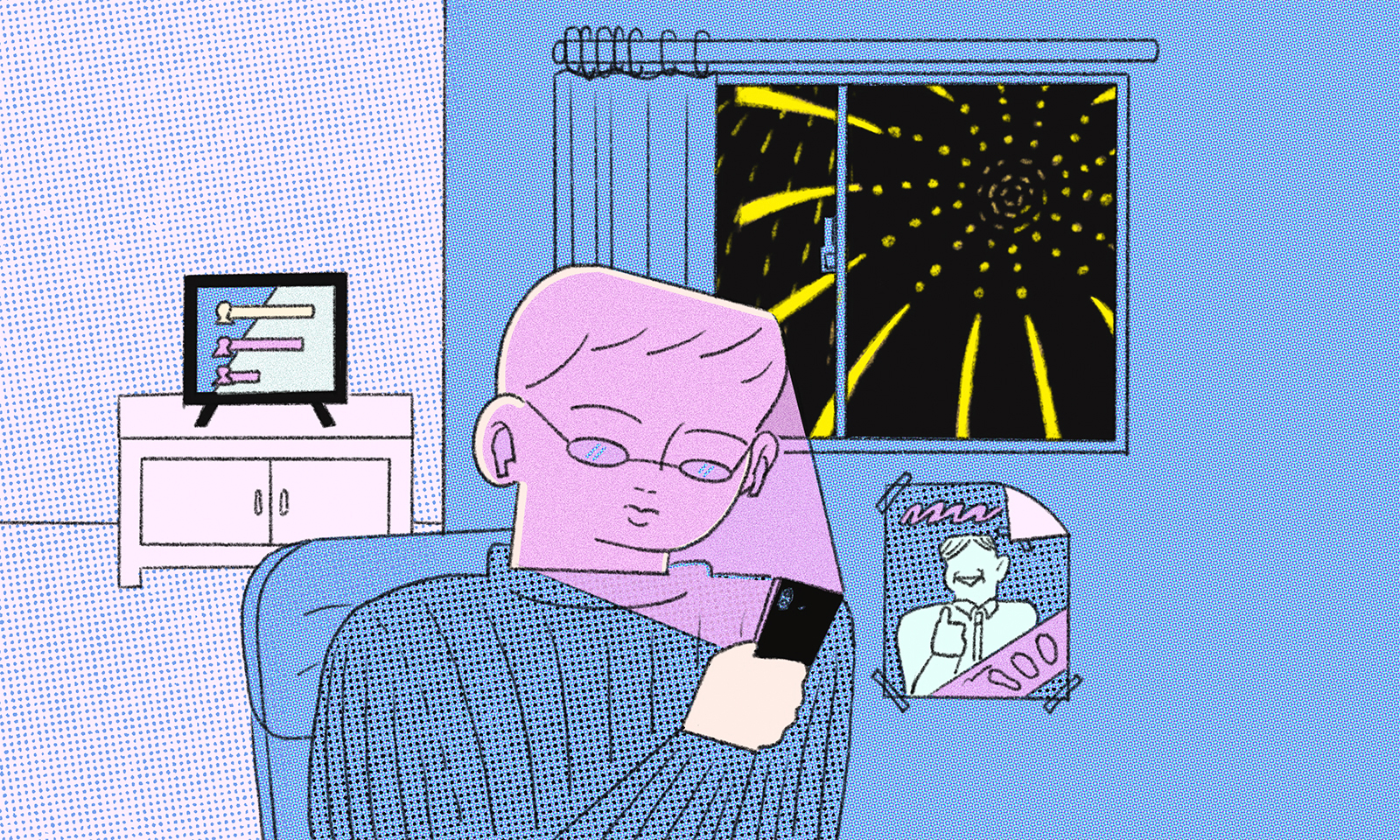
敗選的事|身為相對少數,我們未必孤獨 ft. 馬世芳
這輩子第一次作為成年公民行使投票權,應該是 1992 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那是「國會全面改選」終於實現的首次立委選舉。說也奇怪,我完全不記得那次投給了誰。
那年我大四,再半年就要畢業。1990 年的「野百合」、「反軍人干政」,1991 年「獨台會案」引發的「大學生佔領台北車站」與「廢除刑法一百條」抗爭,我都到了現場,卻算不上熱衷的參與者——那幾年,社會實在是熱鬧,大學生時不時上街遊個行,靜個坐,並不是什麼值得說嘴的事。
我很想說:當時已經經歷了改變人生的政治啟蒙,從而形成了堅定的認同與信仰云云,但事情並非如此。政治認同的前提是世界觀,而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翻騰激變的台灣,我連描述當下的語言都還沒有學會。
更深一層的心理,可能是對那一套一套教條、規訓的語言始終無法接受吧?教條與口號不能令詩與歌的信徒改宗。那時候林懷民說過的:「你叫莫札特入黨幹什麼?」——君非莫札特此一認識之必要,但入黨總是可以先緩緩。
那年頭,學運戰鬥文宣總是喜歡「惟有⋯⋯方能」的句式,彷彿公理正義是一則只要推導就能實現的數學證明題。我卻忘不了羅大佑唱的「如果沒有繽紛的色彩只有分明的黑白 / 這樣的事情它應該不應該?」,Bob Dylan 唱的「每個人都在大吼 / 問你站在哪一邊?」,還有村上春樹寫的「他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國家權力,而是缺乏想像力。」——我想在「他們」眼中,我大概是反動而虛無的吧。
我對自己說:我要保持一段禮貌的距離。我在托洛斯基自傳讀到他常引用史賓諾莎的名言:「不要笑,不要哭,要理解」。其實「不要笑,不要哭」一點不難,甚至很可以作為冷漠與虛無的藉口。「要理解」才是關鍵,而我總在這一句放過自己。
想當年我的同儕,有不少在大學時代已經投身政治工作。有在左翼陣營搞工運的,有替反對黨議員當助理編刊物的,有辦讀書會培養高中生接班梯隊的。學生自治組織和校際串連的爾虞我詐派系鬥爭,江湖幽深,在我眼中簡直可比「聖堂教父」,他們在政治上(還有許多其他方面)都比我早熟。
後來我遇見過不少在某些領域非常厲害,政治認識卻非常幼稚的大人,這才慢慢體會:政治不像人生其他事情,它未必會隨年歲累積經驗與智慧。多投幾次票,並不表示你的選擇會愈來愈高明。
然而,怎樣才算一個合格的公民呢?怎樣才能在漫天空頭支票、煽情話術、仇恨動員、還有各種先射箭再畫靶的滔滔宏論之間,找到判斷的理據呢?
1994 年首次北高直轄市長民選,陳水扁、趙少康把一場市長選舉拉高到總統選戰規格(至於我們能夠真正投票選總統,是兩年之後的事了)。我在左營當兵,寢室裡同梯展開統獨大辯論,激動得幾乎打起來,差點被抓去關禁閉。我記得投票前夕台北街頭,插著新黨旗幟的汽車大聲播著戰歌呼嘯而過,馬路中央安全島上有人激動地揮著國旗。
1995 年退伍,獨自赴倫敦、巴黎旅行,台海爆發飛彈危機,洋人聽說我從台灣來,都露出面對難民的同情眼神,問你們那裡是不是要打仗了?——不想將近三十年後,我們又在面對似曾相識的情境。
1996 年首次總統直選,李登輝、彭明敏,還有國民黨內政爭落敗的林洋港和郝柏村脫黨參選。李登輝以 581 萬票勝出,都說是共產黨助選有功。
我沒有投阿輝伯,也沒有投彭明敏,更沒有投林洋港。那一次,我投給了第四組候選人陳履安——陳誠的長子,國民黨「四公子」之一。開票之前,我甚至幻想他搞不好會當選,應該有很多人跟我一樣厭惡政爭,期待「清流」吧?對,二十五歲的我,政治認識就是那麼幼稚。當時報紙分析選情,都不知道究竟誰會投他,只好寫:陳履安和搭檔王清峰一心向佛,佛教徒大概會投這組吧!那一次陳履安拿了 107 萬票,得票率 10%,佛教徒們顯然也並不都買單的。
1998 年陳水扁爭取台北市長連任,競選總部成立「扁帽工廠」開發週邊商品。繡著戴帽小橘人的「扁帽」綠色毛線帽大賣特賣,滿街都是戴「扁帽」的年輕人,地攤夜市還出現許多仿冒品,台灣選舉史上第一次靠週邊商品創造了巨大經濟效益。大概要到二十年後,韓國瑜的「韓粉」週邊效應才足堪匹敵當年規模。當時女友後來的妻出身高雄深綠家庭,準岳母加入「水噹噹姊妹聯盟」助選,到處趕場。有一大隻扁帽娃娃,現在還擺在岳家的鋼琴上。
大概也是這次選舉吧?瓦斯喇叭成為選舉造勢場合必備的道具,囂張無禮,令我深惡痛絕。
阿扁市長任內發生十四、十五號公園反拆遷運動和廢除公娼爭議,我無法像準岳母那樣為他熱情助選,但終究還是投了他一票。開票之夜,施政支持率高達八成的阿扁敗給了馬英九,支持者哭成一片,然而當場就有人喊「總統好」、「選總統」。那天我是什麼心情,現在記不得了。
阿扁落選感言那句傳誦一時的「對進步團隊的無情,是偉大城市的象徵」,我猜是文膽林錦昌寫的——阿扁口才極之犀利,文筆卻不算好,得靠文膽代筆。那年和幾個朋友一起編寫了《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出版社邀了時任市長的阿扁作序,弄得我們幾個都不痛快。倒不是反對這個市長,而是不喜歡大官來摸頭。那篇文膽抓刀寫的序,好幾年後改版才拿掉。
儘管有些政治人物令我衷心尊敬佩服,但誠實地說,我從來沒有變成哪個政治人物的「粉絲」,落選了也不至於多麼傷心,更不會以為台灣從此完蛋了——這座島歷盡摧折磨難,哪有那麼容易完蛋。
聽過很多家庭因為政治認同而兩代撕裂——冷戰、相互詛咒、離家出走、甚至斷絕往來。我運氣好,家裡人從不干涉彼此的投票意向。我們從來不問彼此投給誰,也不特別好奇。都說宗教、愛情和政治這三件事,最難改變。我們家不拜神,大人不介入孩子的感情交往,更不會管你投票給誰。
只有一次例外:2020 年總統大選,蔡英文在驚濤駭浪中爭取連任,我忍不住在投票前兩天寫了封長信給爸媽,懇切縷述應當投票給小英的理由。然而直到現在,我都沒有問過他們讀了的感想,以及後來到底投給了誰。
2024 年總統暨立委選舉,我不再保持「禮貌的距離」,替台北的苗博雅、彰化的吳音寧競選助講,寫了幾篇催票文。後來她倆都沒選上,畢竟是艱困選區,民調一路看下來,倒也早有心理準備。當選固然可喜,落選也沒關係。來日方長,只要有心經營,這一路累積的能量,總會派上用場。這次好幾個我素欣賞的青年政治工作者落選,心情也是一樣的。
選民服務千絲萬縷,地方政治盤根錯節。我聽競選幹部解釋樁腳賄選何以至今奏效,乃慢慢懂了:選舉是爭奪資源分配與再分配的權力,亦即劃分「自己人」和「局外人」的決定權——「自己人照顧自己人」,在宗族、社群的網絡,你必須努力進入、協助鞏固「自己人」的圈子,成為「恩庇體制」的一部分。那幾個惡名昭彰的地方家族總能穩坐江山,大概就是這麼回事。夸夸其談的文青,注定只能當「局外人」。如何裡應外合、從根動搖這個體制,便是政治工作者的專業,談何容易。
擁有投票權以來,最巨大的挫敗感並非哪次總統大選,而是永生難忘的 2018 年公投綁九合一選舉。那一次投票,市長、市議員、里長、加上十題公投,總共十三題,我的答案「全錯」,零分。
且讓我提醒大家一下:那次公投「民法婚姻必須一男一女」同意票 765 萬,佔 72%。「國民教育不得實施同志教育」同意票 708 萬,佔 67%——那就是陳珊妮後來在〈成為一個厲害的普通人〉唱的:「與七百萬人逆向而來的惡寒交手」。
我痛切體會所謂「同溫層」之虛妄,嘗到站在大多數人對立面是什麼滋味。之後好一陣子,出門買菜、坐公車、搭捷運、吃館子,掃視週圍面目如常的市民,總不免恨恨地想:就是你們反對同婚,反對同志教育,反對以台灣名義參與國際賽事,反對非核家園,就是你們!
然而日子總要過,心情總會緩過來。同溫層大崩潰之後,也會互相支持、接住最失落最痛苦的那些人。我遂明白:身為相對少數,我們未必孤獨。
我在大學課堂的許多同學,因為那次投票而傷了家人的感情。他們第一次擁有投票權,卻發現幾乎整個大人世界都站在自己的對立面,不免悲憤幻滅。他們在課堂報告裡寫滿了質疑和痛苦,我得說些什麼。
我說的大概是這樣幾段話:
知道自己是少數,並不是壞事。真正的考驗,現在才要開始:民主政治沒有那麼便宜,公理正義不會自動實現。若我們仍相信自己是對的,那麼,我們願意付出多少代價,改變這個社會的多數人?
若你因為政治而和身邊人傷了感情,請記得:否定別人的政治認同,等於否定他們多年相信的價值。光靠言語辯論就想說服別人改變政治認同,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哪怕你理直氣壯辯倒對方,人家心裡還是不會服氣。受到羞辱的人,永遠不會變成你的同志。爭取認同,首要之務不是輸出理念,而是同理對方。自己要先嘗試理解對面的人,人家也才可能敞開心門。
不要被仇恨動員。我知道這不容易,面對某些人的嘴臉,我也有恨,甚至能夠同理早年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政治暗殺,真的。但是恨意只會讓你把心門鎖起。在我們的時代,仇恨與羞辱的言語取代了暗殺的刀槍,對立陣營一旦以等量齊觀的恨意相互投擲,同理共情的空間就沒有了。
政治不只說理,也有感性。先動之以情,再論之以理,會比較有效。若是因為政治撕裂、傷心,請靜下來想一想:他們仍是愛你的嗎?你仍愛他們嗎?假如答案是肯定的,就不值得為了這個彼此傷害,畢竟你們擁有更重要、更值得珍惜的東西。
幾年後的現在,看到許多年輕人有了和我未必相同的政治選擇。於是上面那幾段話,也說給自己聽。時時保持同理,若是可以,盡量當一個接得住年輕人的大人。
其實《托洛斯基自傳》我始終沒讀完。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史賓諾莎的原話,還有一句「不要恨」——是啊,不要笑,不要哭,不要恨,要理解。
【馬世芳】
廣播人,作家,電視主持人,一九七一年生於台北。曾獲六座廣播金鐘獎。著有散文輯《地下鄉愁藍調》、《昨日書》、《耳朵借我》、《歌物件》、《也好吃》,曾獲《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書獎、《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等。主編《巴布‧狄倫歌詩集》、《台灣流行音樂200最佳專輯》、《民歌四十時空地圖》等書。曾以公視《音樂萬萬歲第四號作品》獲提名電視金鐘獎最佳綜藝節目主持人。
敗選之後 𝗔𝗳𝘁𝗲𝗿 𝘁𝗵𝗲 𝗱𝗮𝘆 𝘁𝗵𝗲𝘆 𝗹𝗼𝘀𝘁...
你以為民主的世界會越來越好。但事實是票多的贏,票少的輸——十年後回頭,才發現自己經常站在票少的那一邊。儘管如此,手上的選票卻握得一次比一次更珍重,因為你記得台上的人說過,「可以悲傷,但不要放棄」。
他們沒有放棄,你學著在重整與放下之後繼續前進。敗選之後,路還沒有走到終點。









![[閒聊] 大家有在便利商店買過小說嗎? - 看板 BIOS monthly](https://dev.biosmonthly.com/storage/upload/article/tw_article_coverphoto_20250515123328_qj2_thumb.jpg)
